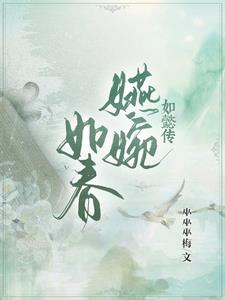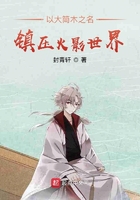第511章 看病,去夜大
孙朝阳终于处理完积压了一个月的工作,把九月份的《中国散文》发行的事情搞定,得了空闲。而何情正好这段时间没有事,二人就成天腻在一起,在城里乱逛乱玩,吃吃喝喝。
没有家里的老头老太太在,日子过得就是爽。
期间,他们找到唐大姐去了医院,找到以前给孙妈妈看口渴心热那个毛病的老中医。
老中医的态度一如既往的不好,当唐大姐叙述自己病情的时候,老头很不客气地打断她,知道知道,你别说了,说了也没用,你是医生吗,还个给自己诊断上了,你身体有什么问题我能不知道。
他这一说不要紧,就惹恼了旁边的唐大姐女儿。
唐大姐和吴胜邦的女儿名字叫吴盼盼,今年十四岁,正在读初中二年级。很叛逆的一个人,这点从她打扮中就能看出来。大热天的竟然穿着宽松版毛衣,还有这个时代坏孩子才穿的扫荡腿牛仔裤,估计是被她父亲溺爱成这样的。
吴盼盼就嚷嚷:“你还是中医大夫呢,中医里的望闻问切晓得吗,你连问都不问,没水平。”
老中医气得嘴唇都在哆嗦,何情忙把她拉去楼下玩。
老中医确实不太想多说废话,这种痛经病人他每天要看几十个,根本就不用多费脑筋,反正就是凭个脉,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下药就是。
他飞快地用笔在方子上鬼画桃符,就把唐大姐给打发了,喊“下一个”前后用了不到五分钟。
看到外面候诊病人排起的长队,孙朝阳头皮有点麻,对唐大姐说:“这是看病?我怎么感觉有点流水线作业的味道。不行,我再去问问大夫。”
唐大姐拉住他,笑道:“不用了,药好不好,吃两副就知道了,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专家,走吧,去药物取药。”
药房在医院门诊一楼,孙朝阳和唐大姐就看到吴盼盼坐在花坛边上,拿着画板画何情,还让她换着姿势,这引来不少病人围观。
八十年代是艺术的时代,搞艺术的人很多,特别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你没有一项业余爱好,就显得没层次。
于是,很多人在学画画,中国画和西画都有。孙朝阳读夜大的少年宫每个周末都要开美术班,欢迎年轻人去学习。给大家授课的老师都很有来头,有次甚至还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来客串。
不过,就算请再好的老师来也没什么用,学生们都停留在入门阶段,上课的时候也就是摆个瓶子罐子、摆个石膏像,让大伙儿画静物。老师也就背着手在旁边看着,兴致来了,就指点一二,说说透视关系说说明暗对比,这些知识小学教材《美术》上就说得很明白了。画上两个小时,散堂,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按照《中国散文》编辑部大林所说的,搞美术和别的艺术形式不一样,最吃天赋。你天生能画,老师说一句就学会了。没天份,就算让徐悲鸿教也是白搭。比如,老师让你画个人物,画出来像就是像,不像就是不像,没有第三种选择。
孙朝阳抬杠:“毕加索不同意你的观点。”
大林顿时闷不着声。
除了美术,现在的年轻人还喜欢玩乐器。大城市还好,小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缺好老师。所以,大多以民乐为主,吹笛子,拉胡琴,弹琵琶。口琴因为携带方便,又便宜,玩的人特别多。大家都是从新华书店里买来教材自学,其中还真出了些民间高手。去年就有个小伙子靠自学,拿了全国口琴比赛一等奖。当时报纸上还报道过,炒得很热。
报刊记者嘛,喜欢搞噱头。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对小伙子的过人天赋和刻苦练习只字不提,只突出人家嘴巴大这一点,说可以直接把整个口琴给含进去,同时吹多个音,自带混响……云云。
孙朝阳也不懂这个,当时看报道的时候也就是一笑了之。但读者却分辩不出真伪,就有一个口琴爱好者跑去医院,请大夫做手术把他的嘴角开大一点,把腮帮子割开,这……实在是太荒唐。
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之所以搞艺术的那么多,孙朝阳总结,主要是物质生活太缺乏,娱乐项目太少,人总得要给自己找点乐子。
等到八十年代后期,电视时代到来,然后游戏机录像机这些新兴娱乐项目进入中国,获取快乐的手段更简单更直接,也没有人再次费劲发展艺术爱好了。
吴盼盼显然是美术爱好者,无论去哪里都背着一个画板。画板是两片胶合板,外面粘了一层绿色涤纶布,还有带子。小家伙一看到好的景色就支起来动笔。
孙朝阳笑道:“唐大姐,盼盼做事挺认真的,了不起。应该画得不错,将来考个央美,当个大画家。”
“也就那样。”唐大姐支吾几句,不想再谈下去。
等取了药,孙朝阳和唐大姐走到两人身边。
朝阳同志探头一看,失惊:“画得不错呀!”
却见,画面上何情一头卷发,戴着花冠,拖地长裙,双眼大得占据脸部一半面积,相当的卡哇伊,仿佛是动画片里的花仙子,又好像是王者荣耀里的蔡文姬。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