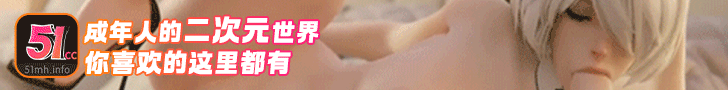地宫在地下三尺,是个阴冷终年不见阳光的所在。
阿蔓比我早一年入的平阳坞,也比我大一岁,比我略高一个头,皮肤浅棕,眼睛细长,眉儿清秀,笑起来露出一口米粒般细白的牙齿。她靠在那祭坛之上,掰了一半冷馒头递给我。
“饿了吧,快吃。”阿蔓笑嘻嘻地将那半只冷馒头塞进嘴里,像吃什么山珍海味一般。
“晚上你来西院,我烤红薯给你吃。”我啃着馒头,虚弱无比地望着满头凌乱的阿蔓。
“阿七,你还好吗?”她忙递过一只牛皮水袋,我接了只喝了一小口,肚子疼得厉害。摆摆手,送还给她。
阿蔓叹了口气,“你是不是……那个了?”
我捂着肚子,凄然地望着她。
阿蔓拉起我的衣袖,手臂上道道或新或旧的伤疤,触目惊心。
“还疼吗?”她看着我手臂上的伤,眼里满是疼痛。
我摇摇头,麻木了。
家主每天熬那些难闻的药,逼着我们喝下。那些药汁里混杂着各种五花八门的毒素。每月隔三差五地从这地宫下水道抛出去的死尸也都是形形色色的。家主疯了,一个有着万贯家产、贤妻孝子、名声煊赫的大家之主竟然沉迷那下作的练功之法。
西院小厨房,亮着萤萤之光。
阿蔓蹲在灶台下,看着我从灶堂里取出两只又大又焦的红薯,两眼冒光。
“好香啊!”她赞叹着,我扔了一片枯荷给她。她用荷叶裹着滚烫的红薯,剥掉上面一层焦透了的皮儿,热气和香气扑鼻而来。
两个人蹲在温热的灶台下,偷摸地啃着红薯吃。
“好啊!又在偷吃!”那人掀开那草席编织的门帘,一手提着一盏琉璃灯,一手抱着一只明黄纸包手指上还勾着一只酒坛,一袭白衣如溯风回雪,头顶上那红色绸缎在晚风中微微拂荡着。
“少主。”阿蔓忙爬起来,微垂着头,不敢望他。
“好香的烤红薯。”他把灯塞给阿蔓,把那黄纸包塞给我,又夺过我手里的红薯,坐在灶台下的小板凳上,掰开那红薯,小口小口地吃着,“好吃。”他一边吃一边夸赞。“快吃啊!特意从太白楼捎回来的烧鸡,还有柳婆婆的糖炒栗子。”
“谢少主!”阿蔓极欢喜地道。
“拿碗来!”那白衣少年指了指案板上的大白碗。
“少主,酒就不喝了吧!”阿蔓看着案板上的那坛酒,有些怕怕地道。
“怕甚?这酒是萧似雨送的,我也没喝过,想着好东西总要分着吃才有味道。”他笑着连倒了三碗酒,一人一碗还真是公平啊!
阿蔓极难为情地望着眼前之人,碗里的酒水透着灯光泛着酒香。
“阿蔓不胜酒力,就别喝了。”我端起碗,喝了一大口,酒是好酒,只是……一旦喝下便是要人命的刀。
“好酒要小酌,若牛饮则大煞风景了。”他一把夺下我手里的碗,放在桌案上,酒水微漾,“你们慢慢吃,我就不叨扰了。”他转身离去,门边那道竹帘子晃了许久。
我疼得两眼冒着星光,扶着案台站立不住。
“阿七!”阿蔓惊叫着,忙扶住我,“你明知道这酒喝不得,何苦来哉?”
“不能让他知晓……阿蔓,你扶我回房……”心中针锥般的疼痛漫延至四肢百骸,又似无数的虫啃蚁噬剧痛无比。我痛得瘫在阿蔓怀里,她抱着我,泪水淆然。
“别哭……”我想安慰她,只是使不上力气。
听见凌乱沉重的脚步声,碗碟撞击声。
“她怎么啦?”那声音模模糊糊,像刚煮开的糖水。
“酒,不能喝酒。”阿蔓泪汪汪地道。
……
窗下的藤花呈半红半紫半白之色,娉婷地在风中摇曳着。青藤树下的泥土一片紫黑。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药味儿。阿九提着熏香在房间里除味儿,袅袅香味四下飘散。
“少主,天色不早了,得去上早课了。”阿九提着一只青铜兽足小香炉,站在美人榻前,小声提醒道。
“……”没有声音,只听见藤花簌簌之声。
我慢慢爬起来,环视头顶的素色锦帐,这是在……流云阁。心下惊惧不已,忙跳下榻,双脚酸软,肚子隐隐地痛着。
短案上放着一只红泥小炉,炉子上正煲着什么,香气扑鼻。
傅流云坐在美人榻上,靠在短案前,手上拿着一把撒金纸扇子,慢慢地地着炉子扇着风。
白衣似雪,清逸若流云。
耳畔垂下一条鲜红的绸带,长发高高绾起,额上泛着晶莹的汗珠。
炉子边放着一只莹白玲珑瓷碗,碗里放着一只白瓷汤匙。
“躺下。”他冷冷淡淡地摇着他的扇子,取了案上的帕子盖住钵盖打开,满室生香。
“阿九,跟冯先生告个假,就说……就说我今儿头疼,让他自己也歇上两天。快去,对了,书房案上那盒茶给他送去,省得他在那哔哔个不停。”他舀了一碗浓稠的汤端了过来。
阿九得令忙放下香炉,一溜烟儿地跑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