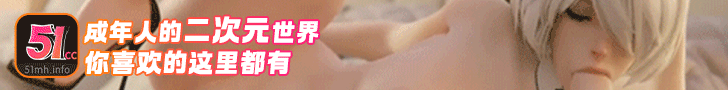是因他有旁的女人,便疑心是他布局?
夕榕的心有些『乱』了。
冰玉突地翻身,跌落床前,跪于夕榕膝下:“梦妃,我知你大义,你能帮帮我么?我不要伴枕太子,我不要违背誓言……我答应了他,除却了他,我谁也不喜欢。”
“你……”话凝嘴边,夕榕看着这个柔弱的女子,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的模样,看她气韵不俗,想必也出身世家,“你且起来说话。”
“我若说了,你可能答应不将此事告诉旁人?”
夕榕肯定地点了点头。
白冰玉重新到榻上躺好,调匀呼吸,才缓缓道:“我是两年前入的宫。是南安城世家大族白家的小姐,虽是庶出,在家中倒也颇得父亲疼爱……”
这样一个如花般的娇女,哪个父亲又不疼爱呢?就是瞧上几眼,都能让人的心为之一软。
夕榕问:“你认得马承徽?”
“认得。”白冰玉答得轻轻柔柔。
难怪马承徽会说把秋梧苑给白冰玉,她们二人之间,莫不是有什么过节不成?
夕榕认真地听白冰玉讲出自己一个管家儿子的爱情故事,青梅竹马、心心相印,和许多寻常而动人的故事一样。只是,他们的爱永远不能表达在人前,只能是彼此小心翼翼珍藏的秘密。
白冰玉一片坦诚,向她叙诉自己已有意中人的秘密,这于深宫、于太子府要是传扬出去,都够杀头了。但她说了,让这样一个深闺女子鼓足勇气道破,又该需要多少的勇气。
夕榕曾经中过媚毒,深晓用理智压下是何等的痛苦,见白冰玉着实痛苦,伸出手指,索『性』点了她的『穴』道。
郁兴站在帘外:“梦妃,红糖和红花都取来了。”
“先喂她喝些红糖水吧!”
大宫娥进来时,看着榻上睡得安稳的白冰玉,正要唤醒,夕榕道:“让她安心睡会儿!”
夕榕出了内室,众人齐声道:“恭送梦妃!”
离了宜雨轩,主仆二人步步行来,夜风一过,夕榕便微微一颤。
郁兴道:“梦妃觉着,今晚下毒的人会是谁?”
“太子那边有结果了?”
郁兴低着头,看夕榕神『色』凝重:“苏良媛认罪了!”
“她……不是在叫冤么,怎的就认罪了。”夕榕面『露』疑『色』,难得真的是苏良媛干的?这样的手法,未免太愚笨了一些。
“苏良媛和白奉仪本是同届入宫的秀女,入宫两年从未得宠。二人在宫中便有过节,苏良媛忌恨白奉仪比她美貌,听说太子‘克妻妾’便想推白奉仪承宠……”
夕榕问:“已经定罪了?”
怎么觉着这里面还有许多未解的古怪。
郁兴道:“喜嬷嬷是这么定的。”
“喜嬷嬷……”夕榕神『色』微凝,喜嬷嬷哪里敢定,苏良媛可是韩妃赏赐的人,思来想去,怎么也觉着这件事,终是透出些许古怪。
只是,到底哪里不对呢?
是哪里?
夕榕移步缓行,郁兴紧跟其后。“郁兴,与我讲讲马承徽与太子间的事?就说说马承徽携良『药』、太医奔赴千里去军营探他的事吧。”
郁兴一愣:“梦妃怎的问起这件事了?”
她足不出户,回抵帝都前,喜嬷嬷和大管家也叮嘱过府中诸事,不得在夕榕面前提及太子宇文昊与其他女人的事,即便是马承徽的也不要提。
她在等,等郁兴与自己讲些什么。
明明很想知道,却不晓该问何人。
喜嬷嬷和大管家对宇文昊忠心不二,要是想从他们那里打听出什么,难如登天。
郁兴小心地看着四遭,确定无人,才低声道:“梦妃回府前,喜嬷嬷便已叮嘱过灵犀阁上下,休提殿下与马承徽的事。”
“那么……你今儿也不打算告诉我了?”夕榕神『色』一凛。
郁兴笑道:“旁人问,奴才自是不说的。梦妃问,奴才当如实禀报。”
郁家上下受过夕榕大恩的,视胜恩人。若不是夕榕,郁母的病难愈;若不是夕榕,郁大隆也难与祝小姐喜结良缘。
“哦。”夕榕低应,“你还算知晓。”
郁兴想了一会儿,主仆二人行得缓慢,道:“那是前年夏天的事。某日,马孺人突听到一个消息:太子殿下在军营因负伤过重病倒了。那天晚上,马孺人彻夜未睡,宫门刚开,她就托了大管家去太医院请太医。又用了一天的时间准备好各种治愈伤痛的良『药』,说服太医,乘车前往军营……听人说,得大半月才抵达的军营,她仅只用了九天,不吃不睡,只顾赶路,待她到军营时,她自个就先病倒了……”
一个女人,虽是他府里最卑微的妾侍,千里之遥,带太医、良『药』而至,任是铁石心肠的男子都会感动的。
“马承徽不过在军营呆了五天,刚能下地行走,就被殿下强行赶出了军营。唉……听她身边的侍女碧花说,当时连她也替马承徽委屈,没想马承徽反说只要殿下康复,便是她最大的快乐。”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