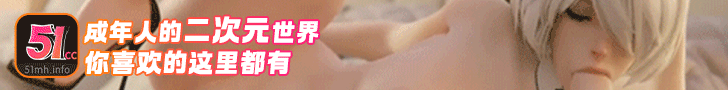就如她言,这一切都是天意弄人。
“小姐曾与我说过你,她说她忘了一个极重要的人。可是当她忆起时,你已经不在了。那日在小姐的生辰酒宴上,我瞧见了你,便猜想你若是她念着的玉公子该有多好,也许这样,她就不会被迫嫁予太子。可是小姐说,她已经问过你了,你说你不是玉公子。自从我家夫人过世后,小姐就未真正开心过几日。璃王若是不信,可以去玲月楼一探究竟,旁的,代芹也就不说了。”
去,当然会去的!
代芹何时离开,他竟不晓,过往与她走近点滴又涌现脑海。记得与她在无垢山庄里一起做纸鸢,一起『荡』秋千……一把大火,他将过往纯洁无垢的自己埋葬。
夜暮之后,他潜入玲月楼,方才瞧见那座凉亭便叫做“无垢亭”,再入阁楼,在二楼的轻纱之间,望见了一块黑『色』的灵牌“亡夫玉无垢之灵位”,有焚过香的印记,在灵牌一侧挂着幅画像,依然是自己昔日模样,从那画的时间来看,已有半年多之久。
亡夫,她竟称他为亡夫。
泪,不由自己的奔涌。瞧见这一切,他才方晓误她多深,伤她多重。
他因恨,一袭白袍换红衣。
她因愧,因为爱,弃下五颜六『色』装,唯着白衣。
她是在追忆那个逝去的玉无垢,而他还是那个她记忆里的玉无垢么。
他算计她,伤害她,就算拿定了离开要死的念头,也不忘让一个女人去代自己伤她、算计她。
“为何是这样?”宇文旻捧着灵牌,一阵撕心裂肺般的刺痛。
他不求荣华,不追富贵,唯愿能与相爱的女子厮守一生。
可他,却那样深的伤了她!
“啊——”他张臂一喝,痛断肝肠。
她为他设想得不可谓周详,他不曾知晓,当她忆起一切,她是回过无垢山庄的,还为他重建的那里。
宇文旻离了思月楼,怀里抱着她给的锦盒,一步深,一步浅地走在街巷中,身后跟着他的贴身随从,谁也不说话。他满心落漠,方然知晓,天意与他开了个莫大的玩笑,他恨她时,他离开扬州,夕榕竟然回过那里。
难怪,难怪……
昔日家奴从江南传来书信,说是有神秘人重建无垢山庄,仿佛那一把大火如梦一场,因为那里又恢复曾经的模样。
那样的房屋,那样的小桥,那样的凉亭、花木……
不再如曾经那般冷情,据说那里住进了一群可爱的孩子,最大的是个不到双十年华的少年,他们在那儿追逐、嬉笑,亦留下了一串串快乐的笑声。将他爱着、恨着、怨着的无垢表成了一个乐园。
夕榕,夕榕……这个名字千百次的涌现心头,唤出却是这般的艰难。
回到璃王府,他静坐在花厅,不语不看,眸光呆直,只一心念头着夕榕。
内侍太监小心入内,低声禀道:“璃王殿下,五皇子到了!”
“五弟!”宇文旻回过神来,原本呆直的眼神有了一抹异样的光亮,定定心神,将锦盒收好,道:“有请!”
五皇子步入花厅,审视一番,抱拳道:“三哥。”
有下人奉上茶点,只余一个心腹太监在旁服侍。
五皇子长长叹息一声:“真没想到,太子居然会这么做?丝毫不顾南、北战事,大齐安危,执意从途中带走了梦妃……”
宇文旻心下正痛,又听五皇子句句言说到太子,提及夕榕,越发痛得彻底,却依死死的强忍着,不让自己流行颜『色』。
五皇子说了一会儿,见宇文旻不言话,轻笑道:“三哥真是好脾『性』,到了现下还能如个没事人。记得几月前,我府里一个不算得宠的姬妾病殁,我都难过了三天呢,三哥如此重情,倒也能像个没事人……”
“你今天来,恐怕不是与我说太子的事罢?”宇文旻冷喝一声,打断五皇子的话。
五皇子尴尬一笑。
宇文旻一脸俊俏极致的面容依如春花秋月般,那双漆黑的眸子里隐藏着的情绪,令人瞧不分明。许是他太过妖妍,也至见到他的人,都会被『迷』住。一个男子能美到无以伦加,美到比女子更如花似玉,真真是个世间妖孽。
宇文旻的语调平缓如常,揭开盖碗茶,吹走上面漂浮的桂圆,道:“听说太子在西北连夺三座城池,照如此速度下去,用不了多久,便能攻下梁京。梁京一旦失守,便夺下了大半个西梁国。你受伤装病事小,没想太子倒立了不小的军功,如此一来,你往后想再动他,不是更难。任你是韩大将军的外甥,韩氏一族里,也并非个个都向着你,那些期盼在战场立功受封的韩氏庶子们,个个可都是偏着太子的。”
韩氏庶子,如韩成、韩和,对于他们来说,承继祖辈、父辈的世袭之位无望,要建功立业,唯有沙场分晓,立军功。而他们更会省时度势,明白自己未来荣华的大树、靠山是当朝太子,而非五皇子。
五皇子本想看宇文旻的笑话,没想被他一语中的。这也正是他来找宇文旻的原因,他慌神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