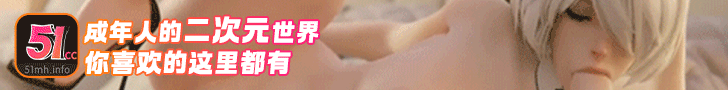傍晚,邱太太和胡浓浓来到金悦府,周坤开车送她们,在门口,他没进院,透过栅栏和梁纪深打了个招呼,“我晚上有酒局,十点半来接浓浓。”
邱太太喜滋滋下车,“恭喜啊梁先生。”
梁纪深不咸不淡瞥她一眼,没搭腔。
胡浓浓捅搡她,“中海风头刚过,梁氏又惹麻烦了,你恭喜?”
“我是恭喜梁先生和小何重修旧好。”邱太太大声喊,“不枉费我在冀省等了这么多天——”
“你教她学点好。”梁纪深又扫了她一眼,“你折腾老邱的招数,少教她。”
“那怎么是折腾呢?”邱太太恼了,“是情调,是闺房之乐。”
吃完了晚饭,邱太太嚷嚷着打麻将,她是麻将迷,一个月有二十天打麻将。
胡浓浓也嗜好这口儿,上流圈的阔太名媛没有不爱玩牌的,越是地位高的,越是贪玩,在牌桌被众星捧月,争相喂牌,哄着赢。当然,是关系不熟的,纯粹替自家丈夫应酬对方的丈夫,关系熟了,不考虑喂不喂牌了。
何桑一连输了十几轮,输得泄气了,“你不帮我...”
梁纪深喉咙溢出轻笑,她牌品一向是不大好的,输了生闷气,“我帮你,她们不乐意。”
何桑犹豫打出二筒还是九筒之际,桌下储物柜的手机忽然震动了。
她下意识一瞟,没备注,是一串生号。
红星剧院同事的号码,她基本没存,包括冀省的老东家,她只保存了院长和副院长的号码,交情好点的同事,工作之余也尽量不联系。
何桑习惯公私分开,矛盾少,省心。
不过,她一般会接听。
“何小姐。”
这一句何小姐,刺激得何桑全身僵硬,耳朵仿佛触电了,麻得她险些扔掉手机。
除了梁迟徽,再无人称呼她何小姐了。
她咽了口唾沫,“黎...黎珍,你有事吗。”
男人显然也明白她的处境不方便,没有多言,配合她,“有事,你在金悦府吗。”
她舔了舔干裂的唇,伸手端茶杯,梁纪深也端杯子,手心正好覆在她手背,她惊吓一缩,茶水洒了,梁纪深蹙眉,打量她。
何桑调整好,比划口型,“是黎珍,在胎检——”
梁纪深擦拭她手背的水,她皮肤太娇嫩了,尽管水不烫,也是红了一小块,“毛毛躁躁的,她胎检你紧张什么?”
“女人早晚要经历的...我上次陪她检查,她抽血抽得哭,焦虑得睡不着。”
他表情缓和了,“那不怀了。”
“不怀了?”邱太太瞪大眼,“梁先生真疼小何,您不要儿子,梁夫人能同意不要孙子?”
梁纪深瞧着何桑,似笑非笑的,“我和别人生。”
搁往常,她小脸儿一准垮了,什么玩笑都行,开不得这种玩笑,今天反常,手机换了个方向,从他这边,换到挨墙那边,离他远了。
他不露声色焚了一支烟,夹烟的手架在椅背,烟雾朝门外飘。
“邱太太和周坤的太太在我这。”何桑倾斜着身子。
梁迟徽嗓音低沉,“我要去外地了,临走想再见一见你。”
汽车鸣笛从窗户传来,“我在小区里。”
何桑手心一股一股地冒出汗。
“小何,你牌莫非又输啦?”邱太太发觉何桑脸色煞白,以为她输急了,耍性子了,打趣她,“我和周太太不坑你的钱,我们是坑梁先生的钱呢。”
梁纪深笑了一声,“坑我的钱?你的水平能坑多少。”
“喏——”邱太太得意,拍了拍桌上堆叠的现金,“我赢了几万呢。”
胡浓浓同样高兴,“我也赢了几万。”
“小何,梁先生保险柜的现金,美元和金条,你统统搬来,咱们通宵。”
何桑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我去一趟洗手间,你们先码牌。”
她走到客房对面的公共洗手间,悄悄改了路线,直奔玄关大门。
出来时,客厅敲响十一点的钟声。
冀省的春夜总有露水和扬沙,温差大,白日15、6度,午夜零下1、2度。
何桑迈下台阶,气息一呼一吐,有白花花的雾霭。
街道清清静静的,举目四望没有一辆车亮着灯。
她借口去洗手间,不好带手机,此时联络不了梁迟徽,正要往路口寻他,转角处的一棵榕树后,闪过一抹黑影。
何桑立即驻足。
那副高大清瘦的轮廓越逼越近,黑色的衬衣,黑色的西裤,与漫漫黑夜融为一体,又无声的疏离。
男人短暂地停在路灯下,像是在确认她,又像是给予她片刻,也确认他。
焦黄发白的光线照射得他彻底清晰。
何桑心脏不可抑制地狂跳,几欲窜出嗓子眼,呛得她没由来地咳嗽。
男人行至眼前,“你穿太少了,冷不冷?”
“梁总...”
一门之隔,她听到邱太太和胡浓浓闲聊,听到她们缠着梁纪深,问他中海集团的董事有没有养情人,梁纪深有一搭无一搭的回应,“养了。”“养在国外。”“生了个儿子。”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