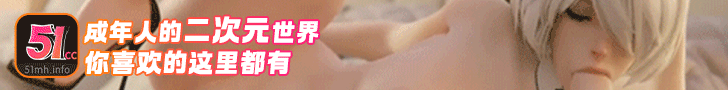佣人撤了多余的椅子,只保留四人位,段志国和老幺坐在正南,何桑陪梁迟徽坐在正北。
发牌员出示了18张牌,没有重复和记号,又调整好桌灯,段志国选了其中的3张,何桑按照梁迟徽的意思,一头,一尾,中间,各抽取3张。
发牌员从剩下的12张牌中,翻开6张,算作场外提示。
“我押大。”段志国搂着老幺。
梁迟徽阖目仰头,活泛肩颈,“不出。”
这局,果然是段志国大7个数。
一方放弃,赢家得2万,两方比点数,赢家增一倍。
接连几局,打了平手,段志国不大耐烦了,“一局定胜负吧。”
老幺先摊牌,“30个数。”
他意味深长笑,“总算开出大数了,梁二公子,认栽吗。”
梁迟徽倾身,看他的牌面,靠住椅背,“我押大。”
“比我大?”段志国扬眉,“你是不是没搞明白玩法啊。”
“开牌。”梁迟徽气定神闲。
何桑掀开,5,10,17。
大2个数。
老幺狐疑打量他。
17。
至关重要的一张牌,力挽狂澜了。
但这张牌分明在发牌员的手上,不在牌桌。
老幺之所以傍上阅人无数的段志国,就是业务能力出众。
在东南亚的赌场,她是顶级的荷官,最擅长“指尖移牌术”了,而且从没曝光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显然,梁迟徽技高一筹。
倒是出乎她意料。
何桑也发现梁迟徽出老千了,小琴的座位抽屉里有一摞新牌,梁迟徽佩戴手铐,手恰好搁在腿间,中途她听到细微的开合声,仅仅一秒的工夫,发牌员亮出所有提示牌,又是一秒的推拉声,大约在这个过程,梁迟徽换了牌底。
佣人,发牌员,从头至尾伫立在牌桌旁,愣是没发现。
梁迟徽出老千的水准不是一般的厉害,一抹,一抽,出神入化的级别。
黎珍说,曾明威经常趁着出差在美国的赌场玩玩儿,那里全球各地的高手云集,堪称赌神打架,
段志国舌头舔后槽牙,啐了口痰,“妈了个巴子。”
“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我们旧日恩怨一笔勾销。”他手摆在牌桌,眼神犀利。
“老覃,请二公子夫人上楼。”段志国答非所问,一手夹烟,一手把玩输了的3张牌。
梁迟徽眼神又寒了一度。
“你在外省有一家地下钱庄,对吗。”四目相视,段志国笑,“我感兴趣。”
“你胃口够大。”
“我今天放了你太太,明天呢,后天呢?”段志国徐徐嘬了口烟,“你这么疼爱你太太,她又这么年轻貌美,你交出地下钱庄,买她平安,值不值?”
何桑看着梁迟徽。
地下钱庄。
广和集团,梁氏集团,云海楼。
梁迟徽这十余年费尽心机摄取的一切盈利,都储存在地下钱庄。
若是交出,他不单单对梁延章无法交待,他亦是白白折腾,白白冒险了。
段志国磕掉灰白色的烟灰,将雪茄塞回铁盒内,梁迟徽忽然开口,“可以。”
何桑怔住。
“痛快。”段志国鼓掌,“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如花似玉的小娇妻,像一朵水灵的茉莉花,换作是我,我也舍得掏钱。”
梁迟徽面目阴翳,沉默不语。
管家拿来一份转让协议书,递给梁迟徽,“二公子,您只要签名,画押,以后段先生与您井水不犯河水,二公子夫人一定安然无恙。”
话音未落,十几个齐刷刷保镖堵住门,杀气凛冽。
“您如果不签,也无妨,段先生遵守诺言,您随时走,二公子夫人继续做客,一旦附近出现一个警察,不要怪段先生撕票自保了。您是知晓的,这种事,在东南亚不是少数,段先生轻车熟路了,有一万个方法脱身。”
何桑垂在身侧的手不停抖。
呼吸也凝滞了。
梁迟徽整个人静止,长达五分钟没有反应。
这五分钟,漫长如同一个世纪。
段志国没催促,等他抉择。
这时,大花臂从外面进来,附耳汇报了什么,段志国拧眉,“瞧仔细了?”
“没错。”
段志国吩咐老覃,“暗室。”
管家迅速卷起一幅字画,扳动花瓶,牌厅的地板是一个升降台,缓缓下降,与此同时,扩建的内二层阁楼也降下,加固的金属脚架钉在墙壁的四角,形成一个会客厅的布局。
直到阁楼严丝合缝嵌入牌厅的位置,消失匿迹。
......
段志国拨开客厅的窗帘,朝院子里一瞥,黑色的红旗L5正对窗户,一个身材英武的男人下车,他表情骤变,“不是梁璟,是梁纪深。”
“他不是弃政经商了吗?咱们不怕他。”大花臂不知天高地厚,“他要是不识抬举,连他一起绑。”
“动了他,我们都回不了泰国,出不了冀省!”段志国是聪明人,神情慎重,“梁纪深在泰公馆失踪了,方圆五公里地毯式搜索,一个脚印,一根头发不会放过,是省里的头号大案,你懂个屁!”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