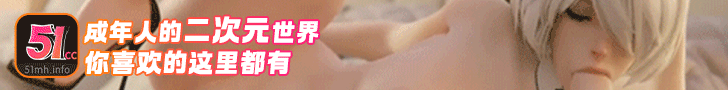陈长安自然看得出对方心思,嗯……赵明远身为青州衙令,还算有几分资格摆态度,可你个小小的主簿站出来跳脸合适?
他看向主簿黄兴的位置,惊堂木重拍:“既是有病便辞去职位,免得耽误政事,现在立刻马上,听到没有?”
黄兴不由的打个激灵。
赵明远梗直脖子:“陈大人好大的官威啊?你乌衣卫是了不起,但这里怎么说都在青州地界,黄主簿是州衙老员,身上有点病状再正常不过吧?岂是说罢免就罢免的?”
“不能?”陈长安起身。
“不能!”赵明远针锋相对。
“刷!”
破风声中白光掠过,青州州衙主簿黄兴惨叫了声,右边耳朵掉落在地,藏名钉入他后面墙壁,余力未消嗡嗡作响。
“陈……陈长安,你……!”
赵明远眼红脖子粗的叫嚣,到一半又戛然而止,文人骨子里都有种懦弱在,他只是仗着地头蛇的优势压强龙,万万没想到陈长安会动手,要真细论,乌衣卫的身份在长安城不算什么,到地方却是能拍死许多官的。
毕竟当初连雍州刺史胡唯坚对陈长安都毕恭毕敬,当然了,那时的陈某也还有奉旨查案的特权。
此次青州休职期间,自不能与雍州刺史之类的相提并论,但再如何差,都轮不到个小小衙令亵渎。
而赵明远呢,偷瞄几眼公堂外看热闹的百姓,总感觉他们在嘲笑自己,面子挂不住,只得鼓足气道:“陈大人,你说的,要在一勺茶叶泡开的时间内证明田二虎有罪,倘若做不到,就是扰乱公堂。”
他的计划是,避开锋芒,待掌握有把柄后再报仇不晚。
“自然!”
陈长安带着略有几分玩味的眼神看了看他,惊堂木再拍:“来人,把屠夫和田二虎带上来。”
很快,衙役们将涉事的二人押到公堂,与此同时,失掉只耳朵的黄兴拿出茶杯,用小玉勺挖盛出一勺铁观音,倒入,冲水。
待铁观音飘浮起来,水肉眼可见的呈现出碧绿色,茶叶开始舒展,伴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会慢慢沉到底下去。
陈长安所谓的一勺茶功夫,便是在茶叶全部沉到杯底前,证明屠夫清白,田二虎有罪。
“大人,我……我冤枉呐!”屠夫开口申诉。
“住嘴!”
陈长安喝断他,手提锃亮的藏名来到二人面前,指住田二虎问:“虎子啊,告诉本官,案发当晚,也就是上个月16日,你在哪里?”
“大人,案发当晚草民在邹记酒馆喝酒呢!”田二虎回答。
陈长安又问:“喝的什么酒,可有喝醉?”
田二虎:“高粱杂酒,有喝醉的大人,所以我回家之后倒头便睡了!”
“哦,这样呀!”
陈长安手拿卷宗边阅读边漫不经心的问:“既然是喝醉,那么当晚月亮应该很圆吧,否则乌漆麻黑的,你怎么可能认路!”
“是!是!是!”
田二虎连连点头:“当晚月亮的确很圆,不然草民还真回不去呢!”
“撒谎!”
陈长安卷宗一甩,爆喝:“案发当晚青州阴云密布,天空中连颗星星都看不见,哪来又大又圆的月亮?”
“我……我……”
田二虎猛地打个哆嗦:“大人,草民,草民记错了,当天晚上的确没有月亮,我是跌跌撞撞回去的,途中还摔了好几跤!”
“哦,这样呀!”
陈长安恢复人畜无害的笑呵呵表情道:“不要紧张嘛,我只是开个玩笑,当天晚上的确有月亮,又大又圆的月亮。”
田二虎愣了愣,随即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尬笑。
陈长安继续问:“你家中可还有妻室?”
田二虎再不敢胡乱回答,放慢节奏,思考片刻:“没有!”
陈长安又问:“州衙门口有没有柳树?”
田二虎觉得莫名其妙,思考片刻,又开口:“没有!”
“赵衙令头顶有没有屎?”
“没有!”
“你们青州有没有个叫豹子头林冲的?”
“没有!”
“潘金莲睡过武大郎吗?”
“没有!”
“死者的胸房底下有没有个红色胎记!”
“没有!”
“啪!”
陈长安一掌拍在主案,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质问:“大胆田二虎,胸房乃妇女最为隐私的部位,你若不是将她奸杀,又怎么会知道底下没有胎记?”
“啊,这……”
田二虎脸色刷的凉下去大半截,呼吸急促眼神变的慌张,结结巴巴道:“不……不是,大人,草民记错了,死者的胸房底下有胎记!”
陈长安怒斥:“本官早已说过,胸房乃妇女最为隐私的部位,你若不是将她奸杀,又怎么会知道底下有胎记?”
“我……”
“可是……”
田二虎颤颤巍巍的抽搐着嘴皮,说不出半个字来,因为他发现自己不管说有或没有,都没办法开脱过去,这是无解的问题。
陈长安乘热打铁:“你清楚死者胸房底下到底有没有胎记,还敢狡辩说与奸杀案没关系?还敢狡辩?来人,给我打!”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