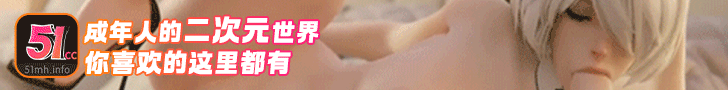第30章 求你留下
正巧安东刚到医院门口,他笑嘻嘻对我说:“别问了,我送的,喜不喜欢?”
我一时之间全身都吓得冒寒气,把花往他怀里一扔,骂着:“神经病!变态!”
他扑过来勾住我一臂,又嗲嗲的撒娇说:“这么快就变心了,狼心狗肺的。”
变你妹啊!
我几乎一拳就往他脸上揍过去,想想又忍了,使劲甩开他手。
安东嬉皮笑脸的一口一个“漫仔”,跟我拉拉扯扯,我站立不稳,跑又跑不掉,正火冒三丈,外面又跑过来一个送花的。
安东“哟”了声,把花抢了,眼珠子转个不停,说是:“原来有小迷妹呀。”
我心头一动,看他抱的两把玫瑰,这两天的期待又死灰复燃。
安东把两把花翻了无数遍,对着那两张小纸片左看右看,我其实比他还想看柏丽今天写的什么?
但是安东一生气,把两张纸都扔进垃圾桶,顺带把两把花也扔了。
我笑眯眯对他说:“你来看我,你见着我还死不掉,可以放心回去了吧。”
安东黑着脸,我看看垃圾桶,有些可惜柏丽的一片苦心。
这天之后,我再没收到柏丽的花,安东也没来医院看我。
出院时我还拄着拐,一直到上飞机回黎城没有见到那个叫柏丽的女孩,安东也把我拉黑。
整整三个多月时间我专心上学,平平淡淡的度过了一段大学时光。
放寒假前,阿文给我发来一条劲爆消息。
说是原木回Z城,东叔和原木一起回去的,下飞机时,遭遇匪徒劫持,原木中了三刀,东叔被刺了一刀,当地警方当场击毙两人,其他歹徒全部逃逸。
阿文提醒我,在黎城小心些,怕这些人跑到黎城来对我不利。
这条消息着实震惊,连东叔都失手被刺,我想起来问他,安然判了几年?
阿文沉默了一会才说:“安然越狱,带着几个囚犯跑了,这回在Z城袭击东叔和原木,就是安然带的头。”
我马上要去台州打第三场拳,Z城出事,难道不是针对我的?
艾伦三个月来破天荒第一次打电话给我,让我不要去打第三场,装病或是自残都行。
他说:“你去了,不但是你,你的家人都危险。”
这句话正说在我心坎上。
原本我是住校,因为安然的威胁,我搬回家住,老泰也专门安排了几个小弟,暗中保护我母亲。
即便这样,父亲在几百里外做工还是出了意外。
父亲的工友打电话回来说只是搭的架子坍塌,一根木头打在父亲头上。
我听得揪心间,父亲在那头赶快喊着:“我没多大事,只是擦破点皮啊,你别跟你母亲说。”
第二日我赶了一天一夜车去到工地,冰天雪地的小城市,工地上坍塌的架子堆了一地。
积雪齐膝,隔着县城一百多公里的山路,医者只是在当地随便包扎了下,连最简单的医疗设备都没有。
我去到简陋工棚,房顶上厚厚的积雪,两厘米直径的冰条子一根根从房檐直垂到地面上,我这个城里人第一次欣赏到这种震撼的奇观。
几人合住的床铺上,又脏又乱,棚子里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我裹着冲锋衣,围着围巾进到里面没觉着一丝暖意。
工友手忙脚乱的收拾着屋子,喜笑颜开的说着:“城里来的大学生,就是精神,看看这气质。”
我一眼看见父亲躺在一堆破棉絮中间,脑袋肿得不成样子,脸上都肿得睁不开眼睛。
他听见有人进来,挣扎着撑起半身喊着:“领导来了吗?我没多大事,躺上两天就可以继续上工,我身子好着呢。”
我坐在床前的小板凳上,拉过父亲的手,摸着切掉的那根小指的疤痕,摸到最多的是粗粝的老茧和布满的裂口。
父亲愣了愣,咧了咧嘴,试探问:“是漫仔来了?”
他慌乱的拿另一只手扒拉眼皮,嚷嚷着:“我说了没多大事,不用过来这么麻烦,你还上学呢。”
工友把小碳炉的铁皮小盖打开,架上锅子给我烧水,拿出我在电视上才见过的上个世纪的搪瓷口缸,抓进一把茶叶。
我躲在房间外面偷偷的哭了一场。
陪了父亲三天,父亲伤势好转些我强行把父亲带了回来。
第三次去台州,我央求老泰留下。
那天是我二十岁生日,老泰来我家吃的晚饭。
那天晚上,我送他出门,两个人步行在雪地上走了好长一段路。
不着边际的谈些闲话,老泰问我:“毕业了想去那?”
我沉默,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他笑了。
他说:“不会真的去考古吧?你这沉默寡言的性子,到是真耐得住考古的寂寞,老古董!”
我被他逗笑了,“那也好过跟着你漂泊不定呀!”
“会不会说?我这叫正当职业,上市公司老总,肤浅。”
“老总!”
我再喊他,“武老总!”
昏黄的路灯下,风中夹着雪沫,仿佛在他的眼中光彩熠熠。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