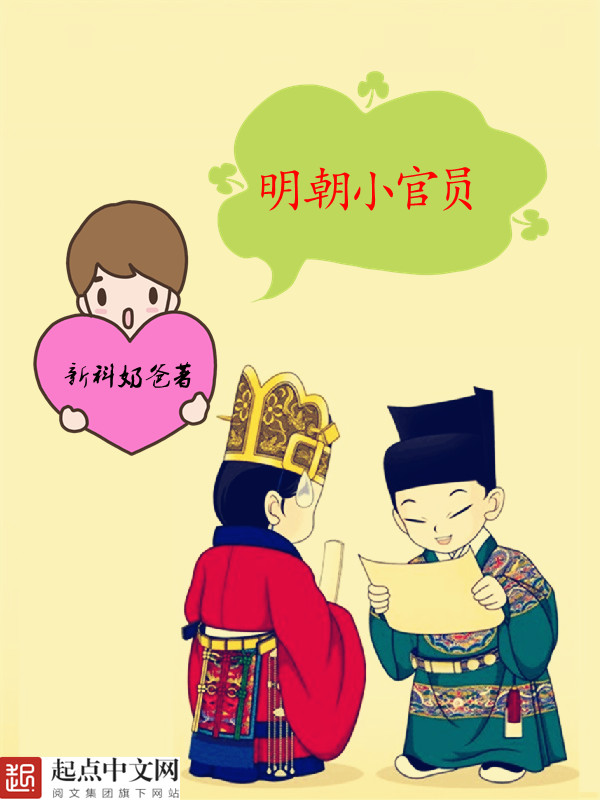刘大夏说完,马文升立刻连连摇头,“不妥,不妥,宣大两镇新立军功,朝廷这个时候清算府库,军心必然动摇,就算你我前去也可能出事呀!”
刘大夏突然间阴阴一笑,“不是有『荡』倭营在吗?”
马文升听完,猛地一愣,他又仔细的思索了一会,突然间猛地一拍,“就这么办,假冒军功,若朝廷一味纵容,早晚必出大事,正好乘机整顿一番。嘿嘿,那些立了军功的,正好可以提拔到京营,给张国丈修坟。”
马文升此说涉及到弘治朝的一个重大的弊病。那就是弘治皇帝有一个很大的爱好,把京营当成施工队,张国丈的大坟前面已经说过,还有什么公主的墓,什么寺庙道观,凡是大的工程,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离不开京营。
虽然京营的战斗力不怎么样,谁都知道,但是这也是皇帝亲自掌握的军事力量,皇帝带头这么干,其他的权贵也是有样学样,整个京营就充满了乌烟瘴气,而把这些冒功的将士提拔到京营,事实上就是明升暗降,调虎离山。这也是兵部为了国家的面子,没办法惩罚这些人才不得不为,想出来的办法。
即便如此,兵部又怕出事,『荡』倭营正好可以起到震慑作用,刘大夏又说道,“那张超怎么办?”
“老夫去大同跟他面谈,就看他晓不晓事了。”
“阁部亲自出马,想必张超会知道朝廷的担忧,此子很识时务的。”
马文升听完,与刘大夏相视一笑,在他们看来,与麻烦的九边武将不同,张超虽然也同样惹事,爱打小算盘,但知道大局,分得清轻重,而且张超的商人脾『性』,让他很容易妥协,朝廷很容易驾驭他。
就在兵部商谈时,刚刚继承父亲保国公爵位的朱晖正在与母亲和妹妹交谈,他作为朝廷使者将与兵部尚书马文升一起出使大同,实际上朱晖还有一个重要任命,他需要带领另外十二团营中精心挑选的几百将官去『荡』倭营学习。
因为『荡』倭营的特殊军制,已经天下皆知,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学习,要不然万一被『荡』倭营训练营拒绝,日后必然前途尽毁,而朱晖作为国公,当然不是这个待遇,他将成为『荡』倭营内定的第二任总兵官,统领这只国家精锐。
朱晖的母亲,老太君见儿子踌躇满志,有些担忧的说道,“晖儿,你已经四十多岁,也颇通情理,现在又继承了爵位,老身本不当教训于你,只是你此次出外,远不同以往,你心中可明白?”
朱晖低下头,很恭顺的说道,“孩儿明白。”
“那你说来听听?”
朱晖开始一五一十诉说起来,与明朝其他的开国功臣相比,朱晖家族的发迹很晚。
朱晖的祖父朱谦是这个家族真正的奠基者,作为土木之变一系列战事的功臣,朱谦作为宣府总兵,立有很大的功劳,而且因为守边,他也没有掺和到朝廷的政治斗争中,所以朱谦最终以抚宁伯的爵位,终老于宣府总兵的位置上。
而朱谦之子朱永则是这个家族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朱永是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军方第一人,虽然比不上王越多立奇功,但朱永作战沉稳,有他带兵,朝廷非常放心,当然朝廷也给了朱家巨大的回报,朱永获封保国公的世爵,可以与大明王朝同休。
现在朱永病故了,被朝廷追封为宣平王,至此这个家族通过两代的不懈努力,终于可以与魏国公徐达的后人齐名,成为大明勋贵的翘楚。
现在家族到了第三代朱晖手中,与父亲朱永当年跟随在朱谦身边一样,朱晖也同样跟随朱永身边,朱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举国上下,朝野内外都希望他成为父祖那样的国之柱石,但是朱晖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
三代为将,必有奇货,这几乎是中国将门的通病,中国上下五千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朱晖也同样知道,所以他十分恐惧,十分不安。在那个没有张超的时代,朱晖数次带兵出征,闹出了很多笑话。
比如某神书大加描写的一场大胜,朱晖就是当时的领兵大将,可是朱大将军的功劳是斩首几级,但是朱晖列出的功臣竟然有上万人之多。所以『逼』的内阁和兵部不断的弹劾朱晖,无他,太不要脸了,丢人不是丢的。
但从朱家的私利来说,他是成功的,他几次出征最起码没有打败仗,朱家的爵位也保住了。慢慢的,朱家也不需要继续带兵,就如其他的开国大将的后人一般,坐享其成,享受祖辈带来的荣华富贵就好,这难道不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吗?
比如说这一次,朱晖就非常清楚朝廷派他出去的目的。与其他十二团营相比,『荡』倭营是张超一手创办,然后辛辛苦苦做大,现在更是辉煌无比,战斗力远在诸军之上,所以张超在『荡』倭营中就拥有巨大的威望,这样一来,朝廷就有些头疼了。
所以『荡』倭营的捷报传到京师之后,大明中枢立刻就形成了一致意见,『荡』倭营现在这种局面决不能继续下去,一定要把这只能打的精锐之师控制在朝廷手中,不是大明不信任张超,而是防范武将的天『性』使然。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