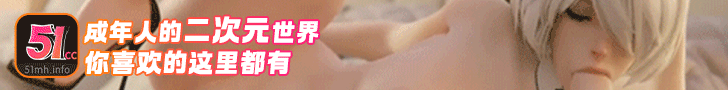葛天是五年前第一次和皓月杂志社签约的,那个时候他刚刚结婚,火气正盛。
在此之前他曾经也是一名专职记者,可是只干了两年,就把那张象征他身份的记者证还给了杂志社,至于原因,连和他同床共枕了好几载的余琦彤也不知道,葛天只说是和同事相处不和。
其实,这只是他编造出来的一个借口。
之所以辞职了,是因为葛天遇上了一件事,令他惶恐不安,甚至病了整整半个月。
那是一个叫做左冷村的小村庄,它窝踞在一座叫坟头山的山脚下,之所以叫做坟头山,是因为山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墓碑,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场,黑压压地罩在了左冷村的头上。
葛天到那里去的目的,是为了查明一桩怪事,一桩警察调查了一年也没有发觉蛛丝马迹的怪事。
小镇子里的警察不同于大城市,如果不是什么轰动全国的大案,他们一般都会草草了事,或者无可奈何地给那些追查未果的案子加上一个响亮又正大光明的名字——悬案。
左冷村的这桩怪事便是警察称作的悬案。
那要从距葛天来到左冷村一年前说起了,和所有恐怖故事发生的背景一样,那是一个阴冷的夜,刮了一整夜的大风,土路上的灰和石子裹挟在风里,呼呼地怕打着地面,时而升到半空,卷起一片阴霾。
村里的狗都在四处狂吠,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某些惊悚的异常。
从远处来了一个人,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离我们越来愈近,最后载倒在了那一片扬起的阴霾里,他的四肢在胡『乱』地挣扎着,他的肩上空空『荡』『荡』,他没有头!
终于,他不动了,天光放亮,殷弘的朝霞混合着他殷红的血,侵染了一整条曲曲折折的路。
第二天一早,一个晨起『插』秧的农民惊叫一声,倒在了那具无头尸体旁。
四五辆警车从镇里急匆匆地赶来了,当天立即开展了调查,直到傍晚,几辆警车才又风风火火地呼啸而去。
死者由于没有头,他的身份难以辨明,而小小的左冷村里一共也就几十家住户,问来问去也没有什么人口失踪的案例,警察在小村子里折腾了半个月,拿个小黑本子挨家挨户地询问,之后,就再没有警车扯着嗓子嚎叫着驶入村子了。
一个不明身份的外乡人死在了左冷村,他的头不翼而飞,这件事情立即传到了城里的一家杂志社,此时,葛天正在赶着一篇关于某女子洗澡时触电身亡的稿件。
一个月后,葛天便被派往了这个叫做左冷村的地方采访。
村子里的人都很热情,听说是城里来的记者都争相恐后地讲起了当时的情形。
一个叼着旱烟的大爷抢先说到:“那天早上四点我去田里,哎,那个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在路上啊就看到了好多血,当时我还以为是谁家在路上杀鸡呢,你看我这糊涂劲儿”,说到这他就嘿嘿嘿地笑了起来,“我还寻思呢,哎,谁家的鸡有那么多血呀,我就『迷』『迷』糊糊地沿着那条血迹一直走啊走啊,你猜我看到啥了?哎,你猜猜,我看到老林头抱着个没有头的人躺在地上!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喊啊,老林,哎,老林,你死啦……”
另一位刚来的大爷突然挤到了葛天的跟前:“你可别听他瞎白话,我那是起的太早了,你不知道,我老伴她打呼噜,一晚上跟打雷似的,有时候我就只好去地里睡,我那天啊……”白话在东北话里是说话的意思,瞎白话也就是胡说。
人群里嘻嘻哈哈地议论了起来,之前的大爷笑着打断了他:“你真行,哎,你能抱着个没有投的死人睡得那么熟,你厉害,你真厉害!”说着他边竖起了大拇指,边斜眼看着葛天。
姓林的老头涨红了脸,想要继续辩解可是憋了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他垂下了眼,嘴里喃喃嘟囔着:“好像你胆子大似的,你们呐,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小同志,你说说,他不是吓晕的还能是啥?”见自己占了上风,之前的那个老头又接着挑拨。
“那您就是林大爷吧?您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葛天把头转向了老林头。
“嗐,你说我倒不倒霉,大早上的,真他娘的晦气!”老林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林大爷,您能详细点跟我说说吗?”葛天问。
“说啥?啊?就是个男的,没脑袋,躺了一地的血,还说啥?”老林头好像有点急了。
“我是想问问,警察最后查出来什么了吗?”
“都回去啦,警察,警察说是要查出来,最后呢,你看看,哪还有人管啦?”一个蒙着土黄『色』头巾的中年『妇』女不满的说。
“哦哦,所以那个人你们都不认识吗?”
“没见到过啊,肯定不是我们这的人”,另一个村民说。
第二天,葛天留下了一张名片便回到了杂志社,他所得到的信息和警察大同小异,无非是一具陌生男『性』的无头尸体,莫名其妙地倒在了左冷村最东边的土路上,除此之外,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