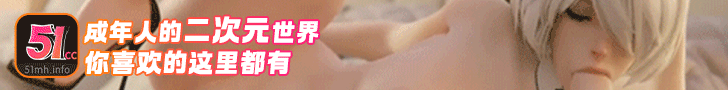自从程府花宴的请帖传出后,各府都开始准备花宴事宜,谁都知道这花宴不止赏花,更是为高门子弟联姻。
孟妧来京师将近两月,除了初来时,孟正棣训了她一顿,让她不得轻易出行之外,之后便没有再说他事,也同意让她出行。只是这京师她初来乍到,倒无多少玩伴可言。
好在孟府所在南居贤坊,有不少文臣子弟,倒可来往一二。
如今孟家同程家同为一体,程府的花宴,孟家自不会错过。孟妧深知这花宴作用,虽有心想以此博取名声,却也不愿因此而嫁与某位公子,便显得不甚在意。
孟正棣却表现出异常的热情。
如今孟太太仍在惠州,在府中打理庶务的是孟正棣一妾室。早就在孟正棣的授意下,为孟妧准备齐全。因府中无正经女主子,便让孟湛随行。
孟妧听到这样的安排后,心里好歹舒坦了些。
这一日,她又命梅疏做了龙眼莲子羹送到孟湛的住处。
梅疏却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姑娘,不好了,湛少爷……湛少爷被老爷训了。”
“怎么回事?!”孟妧猛地站了起来。
梅疏也是满脸焦急之色,“婢子也不清楚,只听到老爷在里头说他……说他不孝,又有茶盏摔碎的声音传来,婢子不敢多留,便连忙跑回来同你报信。”
孟妧一怔。
她大哥一向得祖父看重,哪会轻易打骂,眼下看来,定是情况紧急。
她当即起身,沉声道:“跟我去一趟竹园。”
梅疏应了声,接着便跟她往外走。
……
孟府,竹园。
孟正棣坐在上首,孟湛则垂手坐在堂中。
“过几日的程府花宴,你便同妧姐儿一齐去罢,好好看着她,我之前同你说过的,几位侍郎府上的公子,都可仔细考量一下。”
孟湛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下意识地便拒绝道:“这几日十四殿下事情较多,我需要陪在他身侧处理。”
孟正棣的神色淡淡,冷声说道:“老夫早同你说过,十四皇子那边,不必理会许多,暂且可以放一放。”
闻言,孟湛的脸色更显得阴晦不明,“我如今被陛下任命为十四皇子侍读,为十四殿下做事,怎能不加理会,不为殿下谋事?祖父莫非想让我做那不忠不义之辈吗?”
孟正棣听闻,脸色微变,继而沉着声音道:“你这话是何意?我是你祖父,幸幸苦苦教养你至今,还能让你做那不忠不义之辈?简直荒唐!”
这样的话根本没有说的必要。
孟湛闻言,眼眸愈发深沉,紧紧地盯着孟正棣,面露探究之意。
“去年九月初,十四皇子府长史因病逝世,临走前,曾同我说,八月二十一号那天,他同翰墨书局的伙计相谈甚久,可那名伙计至今却为见其身影。
别人不知道,可祖父应当最清楚,翰墨书局是我们孟家开的。这里头的伙计也是精挑细选的,如何能与皇子府的长史相交为友?且又怎能无缘无故的消失?我想祖父应当是最清楚的。”
听完孟湛这一番话,孟正棣的脸色早已是阴沉如水。
过了片刻,便又沉声说道:“这话你该问蒋松平才对。蒋松平既然敢将十四皇子插手私运之事放出去,可见是十七皇子派来的细作,他的话,你也信?”
孟湛闻言,眼眸里泛起几许冷意,沉声说道:“十四殿下也曾说,蒋长史在八月二十一号那日与翰墨书局是一伙计相谈甚欢,他的话总可以信吧。”
孟正棣面色阴沉,继而说道:“即便蒋松平真与翰墨书局的伙计有来往,又能说明什么?再者,那伙计也未曾失踪,他的尸体早就让人在湖中找到了。”
“这样的话,祖父也只能用来瞒过外头的人罢。”孟湛摇摇头,神色间带着几分嘲讽。“想瞒我这种知晓内情的人,却是不可能的。祖父不打算同我解释一番吗?”
孟正棣的脸色十分难看,却始终不曾多言。只道:“此事没什么可说的!”
孟湛却不打算轻易放过,当即又道:“既然祖父不愿多谈,那不如让我来说道一番。若是我没有猜错,孟家应该是为十七殿下做事才对。
蒋松平一臣事二主,因而深觉妄为君子,无颜面对世人,只得自裁。可我们不同于他,还未酿成大祸,仍有机会脱身而出。祖父又何必做这等自毁声誉之事。”
“混账东西!”孟正棣脸色一变,猛地拍了一下桌面,“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正是因为知道,才有今日一番劝告。”孟湛神色未变,依旧盯着孟正棣,“祖父为十七皇子做事,却又在明面上给程党递投名状,又依附十四殿下做事。祖父可知此为世人所不齿?”
“你胡说什么?!”孟正棣说不出别的话来,只得开口制止他。
哪知孟湛却不听劝,执意说到底。
“祖父别以为现在安然无恙,便可高枕无忧。既然做了这样的事,便该知道总有暴露的一日。届时天下人该如何看我孟家?我尽心为十四殿下谋划,却得一个细作之名,祖父要置我于何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