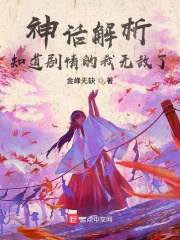孟老太君实在是气急了,忍不住锤起了胸口。
许嬷嬷连忙上前握住她的手,“老太君,您息怒。大老爷兴许是有自己的考量啊,他在京中这么多年,总归知道得要多些。”
“他知道得多些?他知道什么?他不过就是想求得那泼天富贵?”孟老太君冷下了脸,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湛哥儿如今的风采哪里就比那些世家子弟差了,他要是勤勤恳恳,未必就不能走到阁臣那一步,哪里需要依附四皇子,依附程党?他活到这个岁数了,却是连这点都看不清。”
这下许嬷嬷却说不出话了。
说什么?说大老爷确实不该,为了泼天富贵忘了祖训?或者说是老太君糊涂了,谁不想自己更上一层楼,谁不想做那权倾朝野的臣子,大老爷这么做也是为了孟家。
但她什么也不能说,她只是一个下人,主子让你听,那是给你的恩典,哪里就有你说话的份?说到底这些还是他们娘儿俩的事,外人怎么插得了嘴?
说了这么多,孟老太君的心里好歹舒坦些了。
“待会儿湛哥儿从正德院出来后,你让人把他领过来。”
这是有话要交代的意思了。
“老太君歇会儿罢。”许嬷嬷应了下来,扶着孟老太君上了贵妃塌,又往手上抹了精油,帮她一寸一寸按摩起来。
……
都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处在中间倒是不冷不热的,尤其是在岭南这种地方,更给人一种暖意。
一大早,沈余氏就在小书房打理账本,在惠州这些年为了支撑府里的开销,她盘了几间铺子,做了绸缎布匹和胭脂水粉的生意。
掌柜隔段时间就会将账本送过给她过目。
“昭姐儿可用完早膳了?”
“用完了,正在小书房练字呢。”余嬷嬷在一旁回了话。
“她这练字的习惯倒是雷打不动的。”沈余氏一面拨弄着算盘,一面笑,“这样也好,她不喜诗词歌赋,能练得一手好字也是不错,小姑娘家的总要有点才学傍身,不然平白被人说成了教养不当。”
余嬷嬷便笑道,“太太只管放心,姑娘心里明镜似的,哪有不明白的道理?您就别惦记着她把那女师遣走的事了。你的才学当年在京都也是数一数二的,若是亲自教养,不比那女师来得强?”
“我哪是气她把女师遣走?”沈余氏轻哼了一声,“我是气她行事乖张,小小年纪,主意倒是不少,往后还能听上半句劝?”
余嬷嬷免不了安慰一番,“太太哪能这般想,姑娘能有主见,那可是好事。难不成还要像巷子里头的王家姑娘一样,平日里的穿戴都要向人请教?”
沈余氏这回到没有说话了,她的女儿自然不会那般小家子气。
只是未免太有主见了,若是能跟远哥儿一样是个男儿身还好,可偏偏是个女儿身。
前些年那些事也不知道她心里有多少印象。
余嬷嬷自然是想不到沈余氏忧心的缘由,见她没有再提这事,便也闭了嘴,专心打起下手来。
这时有珠帘起落的声音传来,隔扇边守着的小丫鬟传了话进来,“太太,雁如姐姐想见您。”
余嬷嬷立即停下手里的动作,见沈余氏没有异样,便替她搭了话,“让她进来吧。“
于是一个穿着深兰色比甲的丫鬟便徐徐走了进来,朝着沈余氏盈盈一礼。
接着又拿出一叠纸来亲手递过去,低声道:“太太,京师有信到了。”
沈余氏伸手接过,余嬷嬷也有些意外,来惠州府这么多年,京师的信接的还真不多。
沈余氏看着两个不同的信封,不禁惊异,“怎地还有两封信?”
雁如摇了摇头:“婢子不知,只听回事处的人说都是从京师那边寄来的。”
沈余氏看着面上那封,从那字迹便知道这是沈老太爷写的。好端端的,沈家怎么来了信,也不知是出了何事?
……
典雅的小书房里,沈昭正在跪坐在书案前提笔练字。因着沈余氏在余家时一直沿用前朝的跪坐之姿,所以他们家也皆用跪坐。
每日练字是沈昭以前就有的习惯。那会儿她常年守在边关,手上免不了沾染鲜血,身上戾气过重,便时常练字平复心境。
是故,她虽不喜作诗词歌赋,却有一手好书法,更有临摹的手段。
析玉在旁一面替她磨墨,一面说起孟家的事,“听说老太君昨日夜里病了。”
“好端端的,怎地病了?我还记得在寿宴见到她时,精气神好得很。”
“听说晚间开了一扇窗透气,下人们大意忘了关上,老人经不住凉气,竟然受了凉。半夜找来府医服了药,可人还是昏昏沉沉的,如今几位太太奶奶都在跟前侍疾。”
“受了凉?”沈昭手中的笔顿了顿,“我看未必吧。怕是气病了才对。”
“姑娘何出此言?”
“听说孟家大太太虽端庄贤惠,但是在教养方面并不如何出色,况且内宅不言朝事,官场上的事孟大老爷肯定不会跟她提多少,可他在京中的一些情况总会跟他们提几嘴。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