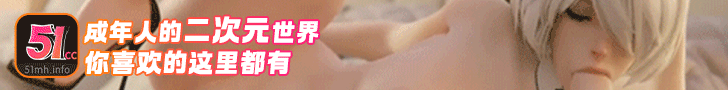沈昭没来得及了解情况。
便收到消息说崇仁皇帝下旨请余怀梓进宫。
虽是小事却也足以震惊朝野。
就是沈昭也有些提心吊胆。尽管这许多年过去,崇仁皇帝对余家之事体现了足够的耐心,可此刻余怀梓堂而皇之地进京,到底有违法制。
她命人去宫外守着,只等余怀梓一出宫,便让人传话回来。可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风平浪静,哪怕众人把御书房望穿,也未曾从里头听出半句斥责来。
而那些打算上折子弹劾的御史们,一时间更是无法抉择。他们心中隐隐冒出一个念头来,也许这京师的天该变了。但要如何变,却无人说得清。
部分折子终是递到了崇仁皇帝的龙案上,只是最后寂寂无声。
翌日一早,沈昭便领着侍书侍画登门拜访。余怀梓眼下住的玉鸣坊乃清流聚集之地,少了嘈杂声,更少了些有意无意窥探的视线,倒是清静。
沈昭坐在骡车里,掀起车帘的一角,细细打量着两侧高大的院墙,清一色的灰白,偶尔有墙皮剥落,却更显得静谧久远,便是从里头探出来的枝干也透着一股幽静,丝毫不觉张扬。
不远处有车轱辘滚动的声音传来,不疾不徐,在这空旷的胡同里虽略显突兀,却又与周遭融为一体。
这车把式水准很高。
她在心里暗想。
下意识地抬眼看去,骡车与他们相错而行,正值清风拂来,吹起绸帘的一角,隐约可见一截绣着暗纹的锦袍。
她还想再瞧上一眼,却只看到平淡无奇的车厢,不免皱了下眉。
侍书两人察觉她的异常,略显诧异,忍不住轻声询问,“姑娘这是……”
骡车已越走越远,滚动的声音几乎听不到。
沈昭摇摇头表示无碍。
心里头却在想方才驶过的那辆车,京师的高门大户都会在车檐垂挂饰品,作自身的标识,以免不长眼的人误撞。但方才那车并无任何标识,可无论是赶车的车把式还是车厢里端坐的主人,都彰显着身份不凡。
这是沈昭在战场出生入死多年得来的敏锐感。
对方分明是有意隐藏身份。
可她在京师混迹数年,对这些高门大宅了如指掌,实在想不出这玉鸣坊能惹得谁来造访。
还用这般隐晦的方式。
玉鸣坊说是清流名士之地,也止于清流,在这居住的人家在士林之中声望颇高,可于官场权势并不得意,也不如何显赫,至多是文官的中层。
沈昭并不觉得此处值得关注。
她压下心底的疑虑,神色如常地跟着仆从进门。
余怀梓早已在庭中候着。
见她过来,便满含笑意地领着入座,“鄙陋之处,也只有这休宁松萝勉强拿得出手了。”
还是一贯喜欢胡说。
沈昭摇头失笑。
“我瞧七表兄神态自若,面含春风,可见此次今上召见,并无大碍。”
余怀梓脸上的笑容敛了些许。
静默了片刻,才缓缓说道:“今上对余家的态度确实过于和软。此次入宫觐见,我原抱着受罚的心思,不想自报端越二字,却让他起了怜惜之念。”
沈昭闻言,神色平淡。
“只怕对当年之事心存愧疚。”
“未必这般。”余怀梓的神色冷淡了许多,嗤笑一声,“许是看我们余家眼下过于可怜罢了。屈于边陲荒凉之地,苟活人世,确实可怜可叹。”
沈昭微微叹了口气,转过话头。
“七表兄今日邀我前来,不只为今上之态度罢。我见七表兄行事甚笃,可是有了应对之法?”
余怀梓见她谈及正事,脸上的不豫之色顿时收敛,沉声说道:“程景濂为首辅这些年,行事微小谨慎,并无大错。但往年权势不足之时,因受之挟,却是劣迹斑斑。”
“受人之挟?”沈昭有些讶异,随即微微睁大眼,“何人?何事?”
余怀梓神色淡淡。
“说是受人之挟其实并不妥当。你可知当年煊赫一时,位高权重的靖安侯?”
靖安侯此人,沈昭自是知晓的。
当初在端阳宴上,她无意中听云礼提及九皇子慕容祁曾随靖安侯修习骑射,但那时靖安侯府早已湮灭。因此事后便着人仔细探查靖安侯之事。
靖安侯之所以被人称为煊赫一时,位高权重,也是有缘由的。
靖安侯祖上是跟着世祖陛下起家,在正始末年的战乱中,居功甚伟,手中又实实在在地握着九边中两镇的兵力,因此虽为侯爵,其风头却更盛国公。
然盛极必衰。
靖安侯想要收敛锋芒,却是为时已晚。不仅许多文武百官视他为眼中钉,便是崇仁皇帝亦想受其兵权。靖安侯走投无路,最后看准了余家。
而余家受过靖安侯恩惠。
正始末年,国朝混乱之时,邯郸亦受波及,余家虽是传承多年的大族,可因未曾入仕,隐于人后,很难不受影响,还是靖安侯当时派遣兵力护住左右。
靖安侯求到面前,余家怎会置之不理?这难关到底渡过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