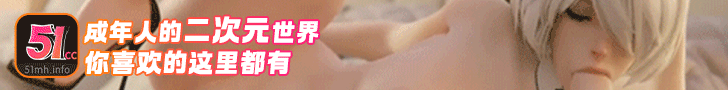如沈昭所言,议论此事的多是高门大宅的子弟,眼下只怕大部分人手里都有已这个消息,更有甚者,还可能会写封信过来确认一下。
果不其然,沈昭一回府,就收到了好几封,猜测的,嘲笑的,善意的,恶意的,全都不少。毕竟眼下风头正盛的沈家姑娘唯有她,而以她当初在狩猎场上的表现,做出这样的事亦不算奇怪。
不过在未查出对方意向之前,她根本不可能给出确切答案。那些信自然也不会回。
……
而在詹事府当值的孟湛,一散衙后,就收到了孟妧递来的消息,刚好是坊间所传沈家姑娘女扮男装进学府读书一事。
他的面色顿时一沉。
头一次没有急着回府,而是让赶车的拐了个弯,折身去了季府。季方平虽常年在扬州为官,却仍在京师留了座宅子。也因程濂力保,并未被收走。
眼下季家老小都住在积庆坊那边的巷子里头。
他下了车,也不询问门房的仆从,径直往里走。好在他时常来季府,对这府里的布局倒十分了解,不必旁人带路,门房便没有上前传消息。
孟湛寻到季槐的书房时,他正在房里作画。近些时日,也不知季槐怎地突然来了兴致,喜欢上作画了。隔三差五的便会拿了一副画给他鉴赏,可惜他素日里事多,并无多少闲情逸致。
却打消不了季槐的念头。
眼下见他过来,也不意外。随手放下手中的笔,又低下头去吹了吹,这才上前将孟湛拉过去,指着那幅画,微微笑道:
“扬浊,你看我今日这颗银杏树画得如何?其实这个时候本不该画银杏的,不过是瞧着院子里的那棵树郁郁葱葱的,极为讨喜罢了。说来——”
“庭植——”
孟湛开口打断他的话。
季槐忍不住止住了话头,继而略微偏过头,刚好看见孟湛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不由得微微皱眉,“扬浊,你为何这般看着我?难不成是这幅画有什么问题?还是——”
“我今日为何来找你,你心里头不清楚么?”孟湛再次打断了他的话。
季槐脸上尚且柔和的表情一点点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冷意,还带几分僵硬,他直起身子,手还落在方才的画上,声音却之前要冷硬许多。
只听他不咸不淡地问道:“哦,那你今日为何来找我?”
“坊间的流言是不是你传的?”
孟湛微侧着身子,盯着他的侧脸,神色间带几分冷漠又带几分不可置信,还余一分失望。
季槐没有动作,顿了片刻,稍显冷漠的声音才缓缓传来,“是我传出去。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那又如何?”
孟湛突然笑了起来,忍不住喃喃自语。片刻后猛地拉过季槐,一把扯住他的领口,然后朝他脸上打了一拳。
“你明知道她是谁,你明知道——为何要放出这样的流言,你这是要毁了她!”
季槐没有闪躲,直接让孟湛打在了脸上,身子后退数步。他抬手随意抹去嘴角流出的鲜血,而后直起了身子,不紧不慢地道:“孟扬浊,我当你是兄弟,这一拳我受了。”
“我要的不是你受这一拳!”
孟湛冷着脸,目光宛如实质盯着季槐。
“我要你把这些流言都澄清了,不许再传这样的话!”
季槐脸上的笑容更冷了些。
“都已传出去了,还要如何澄清?我不仅不会澄清,我还会让人放出更多的话来。她有这么大的本事,还怕这流言不成?!”
“你这是何意?”孟湛皱眉,面露鄙夷之色,“你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一个小姑娘——季庭植,别让我瞧不起你。”
季槐闻言,神色并未有多少变化。
“我何时需要别人瞧得起了?孟扬浊,今日这事你最好别管,若是管了,我们就不必再做兄弟了。”
孟湛神色一顿,过了片刻又沉着脸道:“季庭植,你这是在逼我!你明知道……明知道——”
“明知道什么?!”
季槐打断他的话,挑眉冷笑起来。
“明知道她是谁?你喜欢的人?你可知她是谁?她是云子谦未过门的妻子,与你并无多少关系。你真以为你们之间还有可能?简直可笑!”
季槐眼里尽是嘲讽之色。
孟湛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却是半句话也说不出口。
季槐上前走了几步,见孟湛脸色愈发难看,笑容反倒更甚了些,他慢悠悠地道:“再者,你真清楚她是谁么?你以为就她这样的身份,能入得了大长公主的眼?”
孟湛皱了皱眉,不置一言。
又见季槐眼里冒出几分杀意来,“你可知当初那桩私运案是谁扯出来的?是谁让我父亲惨死在云南的?我今日放出这消息来,可不只是让她难堪而已。
女扮男装去学府求学,可算欺君之罪?你说今上那般厌恶女子读书,知晓此事后又会有怎样的态度?又是欺君罔上,又是入府读书,罪名应当不小罢。若留个全尸还真是便宜她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