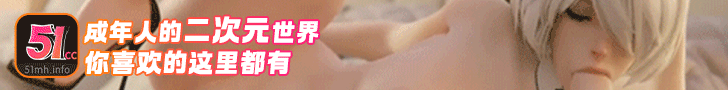不消两日,陆世蒙便上书弹劾大兴县令,斥责其居其位不谋其政,畏权惧贵,阿谀逢迎,视欺男霸女于无睹,罔顾百姓之生死。
众人心里一片了然。
知晓此事关键所在并不是大兴县令畏权惧贵,而是此权贵为何人。崇仁皇帝当即命大理寺探查此事,翌日一早,便有消息传来。
原来那欺男霸女的富家公子竟十四皇子府上的长史之子。
那位长史本是同进士出身,仕途并不顺畅,但是胜在格局颇大,懂得审时度势,因而很得慕容禛看重。入府不久之后,便在大兴置办了田庄,安了家。
可谁知他那儿子却没学好,读书勉勉强强,至今不过是秀才的功名,纨绔子弟斗鸡走狗欺男霸女那一套却学了十足像。
平日里更是拿着慕容禛的名头在外行事,外头之人畏其权势,不敢多言,心中却暗怒不止。以致这邻里之中,多是说十四皇子纵容下属,作恶乡里之事,并无贤名。
崇仁皇帝知晓后当即将慕容禛喊到宫里训斥了一顿。言其知人而不善任,肆意妄为,以致祸患。至于那个长史——纵容下属的恶名都传出来了,崇仁皇帝又怎会让自己的儿子身边还留这样的人?
沈昭听完,不禁一笑。
要说这里头没有别人的手笔,她还真不敢信。每日来往的人这般多,怎就选中了陆世蒙的太太,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此事捅破。
欺男霸女之事随处可见,以慕容禛的能力压一压未尝不可,只可惜对方没有给他这个时间。逼得他不得不放弃这个长史。用一个长史抵过上次在端阳宴的算计,慕容祗这算盘的确打得精。
偏偏慕容禛还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半句多话也说不出。听说被崇仁皇帝训斥后,他又在府里发了一通脾气——因为崇仁皇帝将他府上的人基本上都清理了一遍。
翌日一早,沈昭受云礼之邀去了竹里溪。
云礼见到她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记录病况的纸张交给她。看着她略微诧异的眼神,转而轻声笑道:“你不是总惦记着这张东西吗?怕我心里头避讳又不肯提了。还不如早些交给你。”
沈昭有些意外,心里头却舒畅起来,微微笑道:“还不是你先前总不肯提,我见你这模样——实在是不忍心。”
她接过那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倒没有一探究竟的欲望,毕竟谁都不喜欢提及自己较弱的方面吧。再者,她学的医术不过是些皮毛,偶尔诊个脉倒可以,要是真看起病来,半吊子都谈不上。
她又仔细看了看云礼的脸,微眯着眼笑道:“我瞧着你的气色倒是好了许多,比端阳宴那日还要好些,可见是休养过来了。”
云礼微微颔首,脸上的笑容格外柔和,“你先前嘱咐我好生歇息的事我可一直记着。未免你担心,我自要好生休养。”
沈昭无言以对。
不知是否为错觉,她觉得云礼的心情似乎很好,一点也没有被病痛折磨的模样——脸上再也不是那种带着矜贵与疏远的笑容,而是发自内心的笑。她顿时觉得这样的云礼十分赏心悦目。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她便在心里暗骂了几句,最近真是越来越奇怪。
云礼未曾察觉异样,见沈昭不再说话,便接着话头一转,道:“你之前在心里说发现贺家所行令人生疑,不如说是具体情况。”
还是谈正事时最正常。
果然不能跟云礼说太多题外话,不然心情都变得莫名其妙了。
沈昭心道。
她随即将自己所查到的事告知云礼,“我听析玉说,你曾怀疑贺家贩卖私铁之事另有隐情?”
“同我所料不错。”
云礼点了点头。
“杜巩或者说魏国公确实与程濂有来往。”
沈昭闻言便微微蹙眉,“此事你是何时知晓的?还有宁夏那边……贺家原先不是将私铁运至宁夏吗?那个时候宁夏总兵还是诚意侯,这里头是否会有干系?”
云礼摇了摇头,道:
“宁夏那边我借助顾世伯的人手探查了一番。管地下马市的是宁夏的大盐商,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魏国公的子侄辈作妾,关系颇为亲密。据我所知,运过去的铁矿都是经他的手。
他们宁夏应当还有别的势力,只是一时间查不出来。眼下,又因贺家败落之事,他们对宁夏的处理更为谨慎,又增开了马市,连那个盐商的影子都见不到了。”
沈昭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眼下听他这般说,倒不意外,“如此看来,此事一时半会儿也查不明白。但是程濂同魏国公……他们怎会掺和在一起?”
她不禁叹了口气,又玩笑似的道:“莫非这文武不合只为糊弄陛下不成?”
云礼听闻,不禁失笑。
“话可不能这般说,堂堂一朝天子,若是这般容易糊弄,这大周江山怕只能任人宰割。文武不合说到底还是政见不同,比如武官想将银子花在养马增强兵力上,文官却想着改善民生。”
说着,他又皱了皱眉,道:“贺家之事是我无意中觉察的。我在工部那边亦有眼线,无意发觉贺家每年上缴的铁矿与实际产量不符罢了。顺着这条线才查到他同西北有来往。”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