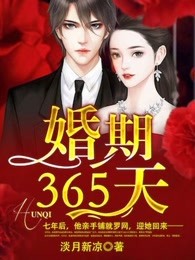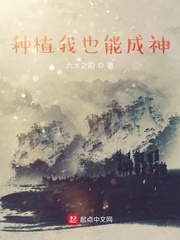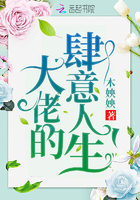在她们刚来那会儿,就有丫鬟备坐上茶了,沈昭跟着孙氏姐妹坐一起,孟姝就走到孟妧的那一桌坐下,说到底她们还是亲姐妹。
说起来,孟妧要是有心,孟姝有这么个出色的姐姐,也算不得坏事,以后定亲出阁时帮衬一下,又有娘家在后边撑腰,日子肯定也不会难过。
“汝宁,你真跟着学了管家啊。”刚一入座,孙析燕就拉着沈昭说话。
沈昭随手取了块栗子糕,细细咬了起来,头也不抬地道:“都说了是瞎胡闹。”
孙析燕还是满脸羡艳,撑着下巴叹息,“瞎胡闹也行啊。总比我每天习女红来得好。”
孙析月听她抱怨,脸色又沉了沉,训斥起来,“你倒是不知羞,习了几个月的女红了,还把鸳鸯绣成了鸭子。”
沈昭听着,不由得扑哧一笑,乐了起来,在她的印象里孙析燕的女红实在是不忍直视,不过对于这事,她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她的也不比人家好多少。
“你的倒还能看出是鸳鸯鸭子来,我的只怕是四不像了。”
孙析燕就在一旁叹息,“你说我们为何要习女红呢。”
沈昭忍着笑没有搭话。
一旁的孙析月听了只觉得眉心突突地跳,心里头止不住叹息,到现在还是这般小孩子心性,往后可如何是好?
她忍不住敲了敲孙析燕的头,“你啊,什么时候能懂点事?”
“我哪里不懂事了?”孙析燕有点不满,又笑嘻嘻地接了一句,“况且,不是还有长姐在吗?”
孙析月听她这么说不由得偏过头去,眼底满是疼惜与无奈。
沈昭见她这般模样,倒是想起了缘由。
“我记得月姐姐年初便定了亲。”
孙析月笑了笑,难得露出一抹小女儿的娇羞姿态来,“日子定在了明年三月初。”
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只是她嫁得远,怕是出了正月就要启程。
沈昭了然地点头,语气里带着惋惜,“只怕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是少了。”孙析燕提起姐姐出阁的事,就有些蔫蔫的,语气里没有了之前的欢快,“母亲说了长姐往后就不便再出府。”
孙析月自己对这事到不甚在意,轻声细语,“总要在家中准备一些东西。”
待嫁的姑娘通常在几个月前就得待在家里绣嫁衣以及准备一些送给男方家人做见面礼的绣品。虽不全是自己动手,却总要起个头。
况且一些为人妇为人媳的礼仪规矩也是要学的。
沈昭听得分明,心里也明白孙析燕真正忧心的不是姐姐出阁,而是远嫁。在她印象里,孙析月是从小就定了亲的,对方是保定韩氏。
九年前,韩家大老爷因故左迁惠州知府,韩家长房随之定居归善县。
因平日里来往甚多,韩老爷与孙家大老爷也兴趣相投,遂结为儿女亲家,韩家大公子与孙析月也算青梅竹马。
不过三年前,韩家老爷回京述职谋了京师的差事,便将长房尽数迁回保定本家,婚事也因此搁置。
眼见孙析月就要及笄,孙家却没有动静,换了信物的事也不能冒然反悔,否则有损女儿清誉。
好在孙家老爷亲笔提信后,韩家没有否认,立即将成亲一事拿上了议程,将日子定在了明年三月初。
可惠州府离保定府数千里,以后想见一面也非易事。
“我记得韩家在几年就迁至本家,如今怕是已经在北直隶扎根了。也不知如今韩家境况如何?”
沈昭问的情况其实也孙家最担心的,远嫁异乡,若不清楚底细只怕讨不着好。
两位老爷关系虽好,可今时不同往日,而且若不是孙老爷提书一封,韩家只怕都忘了这茬,可见对这婚事也不怎么上心。
孙析月也十分清楚她的意思,好在她在几年前就很清楚自己的境况,早已习惯,如今更是半点别的心思也没有。况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她也只能往好处想。
“韩家大老爷和太太都是极为和善之人,听说韩公子也是少年得志,三年前的秋闱还得了解元,明年也准备下场。虽然岭南离北直隶远了点,不过月前,外家小舅已右迁祁州知州,以后到了保定府,也有照应。”
沈昭听她这么一说,脸上的笑意明显比之前要深,孙析月自己倒是看得很清。
“若是这般,也不全然是孤身一人。我还听说韩大公子是长房长孙,月姐姐往后可就是宗妇了。以后上手的事想必会更多。”
听沈昭提起这件事,孙析月难得皱了一下眉。
宗妇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并不好做。而韩家又是簪缨世族,家大业大,打理偌大的后院岂是易事。
更何况还有无数双眼睛日夜盯着,只等着你一朝失足。
而且她未来的夫君只是长房长孙,却不是韩家长孙更不是那个最受宠的后辈。她母亲了解这些事后也曾叮嘱过她许多次,叫她往后行事务必小心,不可骄作。
说来这就是大家族的不好了。
这些思绪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接着才缓缓说道,“近来一直跟着母亲学习管家。好在韩家长辈皆健在,一时半会儿也不需要我管太多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