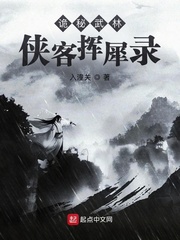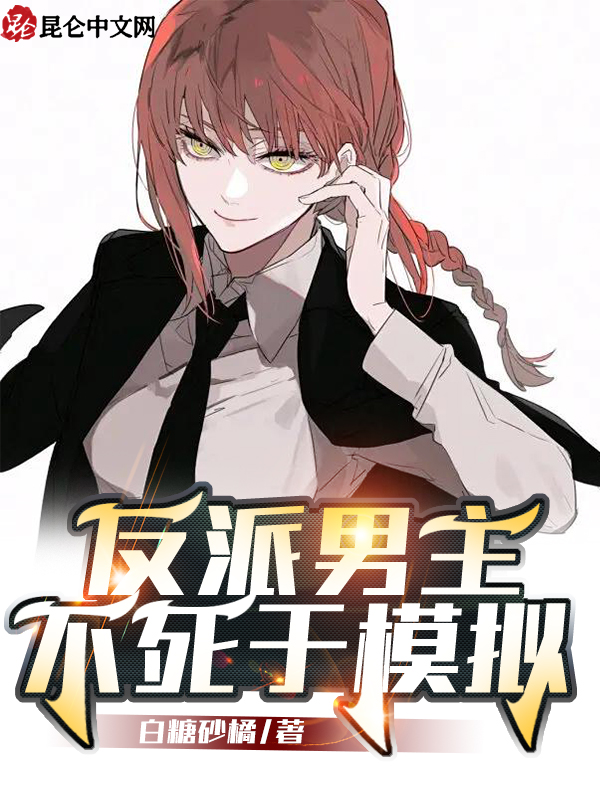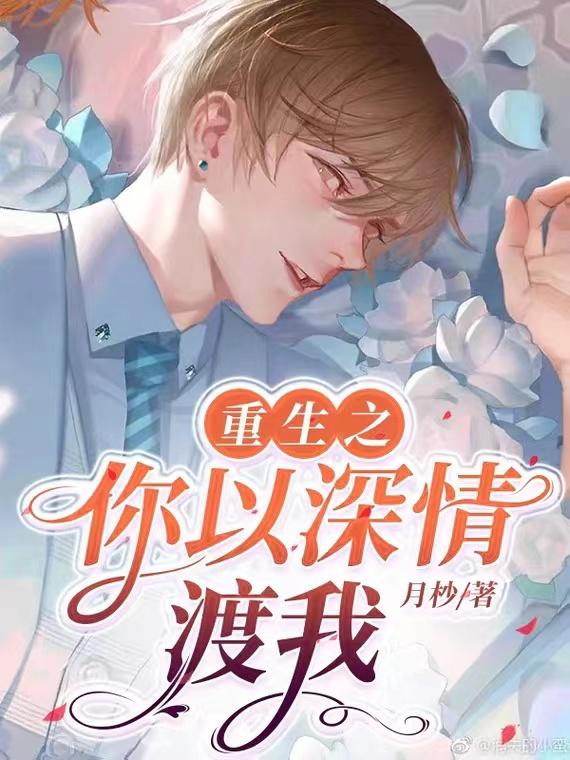宫里头还未传来消息,就传出了崔逊身死之事。
听闻他是自缢而亡。
身后还留了一封书信,上头寥寥几笔——上不全孝情,愧对于亲。下不尊忠义,愧对于友。何以面目存于世?故辞。
证人身亡,死无对证。
季槐准备的大戏只开场了一半,就要无疾而终。听闻他当时恨不得拿把剑在崔逊的尸体上捅几个窟窿出来,被季桐死死拉住了。
崔逊一死,很多事就随着他的消亡而消弥。至少挟持之事没法儿再按到沈昭身上,又因崇仁皇帝有意偏袒,此案不破自解。而崔逊的那些过往……事已至此,沈昭又怎会拿着去刺激季桐,也算全了崔逊的名声。
但季府却没有安定下来。
崔逊身死的第三个晚上,府中遭遇贼子进犯,又乍然起火。幸好府邸安置的府卫不少,否则整个季府只怕都危矣。可尽管如此,季槐还是受了伤。
火势不小,前庭多处受损,甚至于隐隐漫延至后院。而存放崔逊尸首的倒座,更是烧得只剩灰土。
季桐知晓后,扑在一堆烟灰里,恸哭不已。
闹得满城风雨的女扮男装欺君罔上之事最终以一种异常平淡,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而结束。
这个结果实在是出人意料,便是沈昭也不由得多想了几句。不知崔逊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意识模糊的那一瞬间,心中又是否有悔意?
当然,这些定然是不得而知的。
而此时,陆路水路交替着走的陆世蒙,终是安然入京。到了京师,就再无人敢对他动手。但他行事亦未拖延,连自己的府邸都未进去看望一番,而是直接请求进宫面圣。
而崇仁皇帝得知他在福建查到的事后,会有多愤怒,也是可想而知的。
事已至此,铁证当前,谁也无法反驳。崇仁皇帝甚至没有让人前往福建探查虚实,而是直接命人押送潘仪,赵钦等与之相关的官员立即进京受审。
沈行恪连失两县之事亦传至朝堂,这一次,无需沈昭出手,便有御史出面澄清,说是潘仪,赵钦等人与倭寇勾结,有意以污言恶行戕害忠臣。
以沈行恪之能,区区两县,怎会失守?是赵钦将两县的部署全然交于倭贼,才致卫所军士节节败退。又将赵钦与倭贼所通书信呈至龙案。这才保全了沈氏之清白。
与此同时,弹劾赵钦等人的折子也如大雪般飞来。
而站在百官之首的程濂,在被崇仁皇帝问及对福建之事有何看法时,他面色如常,身姿不动如山。不咸不淡地来了句,“赵少恭等人不念忠义,为一己之私行苟且之事,枉为人臣,自要严惩不贷。”
没有丝毫袒护的意思。
偏偏崇仁皇帝又似笑非笑地来了句,“朕见你往日同赵明纪最为要好,此次也不出手相助么?”
程濂面不改色。
“回禀陛下,微臣同赵大人交好,是因朝堂事务需时常商议,并无别的缘由。且虽则此次赵大人并未过多罪责,但其幼弟做出卖国叛君之事。
都言长兄如父,赵少恭不遵法度,与其兄长管教不当,不无关系。因此赵明纪自有不可避免之责,理应一同受罚。臣无力相助。”
崇仁皇帝听闻当即笑了起来,连说三声好。
这桩案子本也没有多少问题。
一过三司会审,基本上就说得明明白白了。几人的罪很快就被定下来。接下来要忙活的则是朝堂官位的变动。
此事事关重大,沈昭不可能单独下决定。案子定下无多时,她便给韩府递了拜帖。自韩廷贤做了工部尚书后,又因得崇仁皇帝看重,权势愈长,府中清望更高,拜访者更是络绎不绝。
好在韩家对她的态度并未发生转变。一接到她的拜帖,便连忙邀她上门,韩廷贤亦是提前散衙,邀她去书房商议事宜。
“沈姑娘今日前来,可是为福建官位变动一事?”
因行事略微匆忙,韩廷连官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在书房同沈昭见面。
沈昭也不同他拐弯抹角,直接道:“通倭案一结束,福建上下就会有不小的变动。且,因沈家之事,我们又同周家有了交情,福建的军务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插手。
若是将巡抚,布政使这两个位子也抓在手里,整个福建都能作为我们的大本营。福建的私运倭贼络绎不绝,虽则凶险却也是机遇,只要我们处置得当,福建定会成为我们都助力。”
京师和地方从来都不是孤立的。
而眼下,韩廷贤等人的不足之处就是地方上并无支援。
手里若能抓住福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笔助力,再者,海上私运那般多,他们总是免不了要同福建官场打交道,届时京师的高门望族就都少不了要联系一番。
“此事我亦想过。”
韩廷贤略微思索了片刻。
“但现在的问题是,从何处来合适的人选,眼下与我们站在一处的官员倒是不少,但未必想去地方,毕竟在福建要做出政绩来,难度不小。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