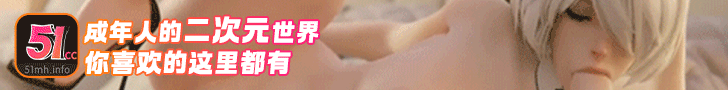沈青潼环伺了一边四周,淡淡地道:“这信里的内容,说给你听当然是没问题的,可是这周围还有别人,哀家是说好呢,还是不说呢?”
一听还有别人,曲蔺华忙四顾查看,但茫茫黑夜,哪来的人影子?
沈青潼直起身子,厉声道:“这信虽是你主子给哀家的,但哀家可没打算念给你听,哀家想你家主子恐怕也不会希望你听到的!”
曲蔺华眸子里的光亮明明灭灭,表情阴鸷得可怕,带了几分恼怒,有人伺机躲在暗处监视着,但自己却浑然不知,实在是不应该!
“到底是何方神圣,不妨现身让人一见,与其躲在暗处受罪,倒不如你想知道什么直接问我吧,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曲蔺华的目光穿过门廊,半眯缝起的眼犀利地扫过四周的寂寂花树。
良久,周围还是寂静一片,没有任何声响,风起拂过花树摇曳,好似没有人存在。
曲蔺华狐疑地望向沈青潼,按理说这伪装都已经被识破了,那偷听者怎生地还不出来呢?沈青潼竖起一根食指,虚晃了两下,然后置于唇上压了压,示意他不要说话。
而后,她站起身走到门口,长袍拖地,衬托出巍巍气势,唇边噙着一丝冷笑,冷冷地道:“敢做不敢当,难道你家主子就这么教你的?嗯……青衣姑娘?”
沈青潼故意拖长了尾音,极具气势却又绵长迂回,像是一把刀有些钝了,老是切割不开肉质,只得来回的切,让人难以解脱。
沉默,两人窒息的沉默,时间一点一滴的走过,没人去计算过了多久,只觉得好像是一百年那般漫长。
回廊侧边的一树万年青蓦然动了动,月光映照着纯白的积雪,那抹绿很是显眼,沈青潼和曲蔺华都注意到了。
“青衣见过太后娘娘,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从万年青旁边钻出一个女子,青色的棉制袄裙,挽起一个简洁的发髻,一支通透清爽的碧玉簪斜斜地插入发间,整个人犹如一块青玉,温婉可人。
正是沈青潼的前任贴身侍婢青衣。
曲蔺华的眉头微皱,考究地打量着青衣,他见过这女子几次,但只是远远地,并未近看过,实在没想到这偷听者居然是她,尽管脸色掩饰得很好,但语气还是泄露了他的惊讶——“是你?”
青衣只是向曲蔺华略略施了个礼,脸上是得体的笑,却无端端让人看得怒火燃烧。沈青潼和蔼地挽过她的手,将她引到床边坐下,眸光里是温和的笑,但那笑意却只在眸海的表层打着转,硬是到不了心底。
“青衣,哀家可是哪点对你不好?”沈青潼这么问,盯着她看,好似想从那张温婉得好似水墨画的脸上看出些许端倪。
青衣面色讪讪,仿佛是想起了什么,眼角略有些湿润,垂了头低低地回道:“没有,太后娘娘没有对不起青衣过,至始至终,太后娘娘对青衣都很好。”
沈青潼冷哼一声,依旧软软地握着青衣的手,但话语却凌厉,眼神也耐人寻味:“真是场面话!面上说过,一会儿便尽皆忘得干净了吧!如若不然,你又怎会背叛哀家呢?”
虽然沈青潼这具身体里面居住的灵魂换了人,但沈青潼照常理推算也知道,青衣到底是跟了太后好几年的侍婢,从沈家一路带到皇宫大内里来,想来主仆之间的关系理应是不错的,不然谁愿意跟不待见的人待一块儿那么长的时日呢,尤其是在主子随便一个抬手便能遣散侍婢的情况下。
因而,沈青潼才说了这样的话。
青衣面色煞白,想要挣脱沈青潼的手,却发觉她用了力,又不敢太过明显地挣扎,潜意识里也怕伤了沈青潼,不断地往后退,直到背部抵住了床铺雕龙刻凤的栏杆,退无可退才堪堪止住。
她死咬着唇,毫无血色的唇上被咬出一排赫赫的牙印,眉色一凝,终是抬了头迎面对上沈青潼的质问:“青衣……青衣也有苦衷的,请太后娘娘谅解。”
“苦衷?”沈青潼嗤笑,她步步紧逼,“那你说给哀家听听,有什么苦衷是哀家不能帮到你,却是隔得那么远的帝君能帮到的?”
听到“帝君”一词,青衣明显身子一怔,惶惶然脸色又白了几分。
见青衣的表情变化了,沈青潼更确定了自己的猜测:“怎么那副表情啊?哀家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帝君陛下是主子,随了几年的哀家就不是主子了,也亏得哀家没再放你在跟前,要不然还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幺蛾子呢,你说,是吧?”
沈青潼愈来愈觉得自己变坏了,老是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从青衣那震惊和低落的情绪中,她能猜到青衣是有难言之隐的,毕竟帝君的命令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胆子违抗。但她还是拿话去激她,想要敲山震虎,自己打不着楚复,那就震震他手底下的人,别把自己当个二傻子,在背地里妄图算计她。
青衣已经像是快要哭了,泫然欲涕的表情令人见之爱怜,但曲蔺华站在一旁,只是冷冷的旁观着,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知自己不过是个奴才而已,便不再随意发话。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