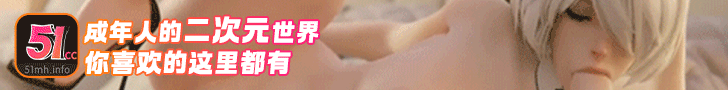她弃了白髦,挑了件蓝『色』的,很快便重新系上了肚兜、中衣,看着帐里的狼藉,心头隐隐痛着。
当她走出小帐,当她和宇文昊争吵,他们之间便再也回不到最初。
是她冲动,还是她在听闻他有了别的女人后,到底忍不住了。
哈庆进了小帐,低头收拾着自己的东西:“梦妃,殿下说,从今儿开始,让奴才去帅帐侍候。”
夕榕淡淡地道:“既是他的吩咐,你只管去吧。我让芸娘过来陪我。”
这一夜的争执,让她倍感疲累。
哈庆走后,夕榕便去了厨房,把瘸腿厨娘给叫过来了。
瘸腿厨娘正在收拾东西,帐外就传来郎中的声音:“草民奉殿下之命,前来给梦妃瞧伤。”
“进来吧!”她坐在榻上,身上盖着小褥,腿上的血一直在涌,原本已经愈合,这一回又震裂开了,郎中褪下缠绕的伤布,道:“还好,不算太过厉害,草民帮梦妃包扎好。伤口很深,草民建议梦妃静养为宜,若是再震裂了,很难康复。”
夕榕未答,只一脸漠然地看着帐帘处。
待郎中离去,她便躺下了,这一躺便一直到次日中午都未出帐,就连午食也是在帐中吃的。
她昨夜和宇文昊争吵的事,对于旁人来说,这是一场闹剧,也是茶前饭后的谈资。
她坐在帐帘前,手里捧着一本书,便这样云淡风轻地翻瞧着。
厨娘走了进来,笑道:“梦妃,要用暮食了!”
她心里很空,昨夜那一场争吵,把她的心全都扰『乱』了:“今儿挺早的?”问完之后,她似猜到了什么,今天一觉醒来,整个营中显得清静,倒是校场和练武场那边却是异常的热闹。“又要打仗了?”
厨娘道:“我就是一个『妇』道人家,也不懂呢,不过瞧这情形怕是快了。”
“芸嫂,一会儿你推我到小山坡上透透气。今儿感觉特别闷。”
瘸腿厨娘应了一声“喏”。
天『色』,一点点地暮下,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白天时,天气阴沉沉的,还卷起了风。夜,浓黑如墨,黑到深处,掩饰不住的脆弱,就是手中火捻子的一点光亮,都会觉得很明很亮。
她是黄昏到的山坡上,带了那件白髦,静坐山坡,一边放置着一盏灯笼。
她只让瘸腿厨娘三更后再来这里推自己,厨娘们很忙,每天起得很早,歇得很晚。若不是她的伤着,她一定又去厨房帮忙了。
听到信鸽落地的声音,她掏出鸽食,笑道:“乖鸽子!快过来,我这儿有吃的。”被人豢养的信鸽,是不怕人的,闻嗅到熟悉的味道,她拍着双翅,在她的肩上停下,夕榕不费一点时间,就捉住了鸽子,从她的脚环处取出一个纸条,喂它吃完,将它放飞。
借着灯笼的光亮,只见上面写着:“太子府姬妾马氏迎秋,乃齐太子女人,于去岁五月入府,不得太子之心。去岁入府的共有三个女人,其余两名皆先后被太子克死,唯独此女安然无恙。安阳大捷前,太子宇文昊因思念失踪的梦妃染疾,此女不远千里,携帝都名医,亲往营中探望。去岁腊月二十六,太子奉命抵京。正月十五,齐宫欢筵,宇文昊拒携马氏入宫,后,马氏求助永安公主,在宫中再遇太子。夜,太子大醉。醉后将服侍跟前的马氏误当梦妃。九月二十,马氏于太子府产下一女,为太子长女,帝欲立为太子良娣,被太子所驳,只晋为六品承徽。”
竟是这样!
他为何不说清楚。
是其间另有隐情,还是他已然对马氏动情。
原本他另有女人,她便不悦,现下又喜欢上旁人,她当真得另行考虑了。
昨夜那一番闹腾,他们已不回去了。
她欠了宇文旻太多,太多。
让她如何面对现下,是与宇文昊重归于好,还是直至淡去。
面对这深深长夜,她心下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不远处,移来一盏灯笼,凝望时,却是渐近的穆槐。
夕榕收好纸条,道:“你怎来了?”
穆槐笑了笑,“瞧这情形,今晚许有一场恶仗,璃王让奴才给梦妃送创伤膏,瞧你不在帐中,想你许是到这儿来了。”
夕榕吐了口气:“今晚三更前,殿下的续骨膏就该到了。”
穆槐着实为夕榕的固执无奈,道:“指头已经断了,又如何重新再接回去,这可不是草木,今年没了,明年还发。”
她低下头,道:“无论怎样,我总是不放心的。就想再试试!”
未曾试过,就说不行,夕榕到底不甘心。
穆槐叹道:“不过才二更二刻,天便这样暗了。”
夕榕尽量说得轻浅些,“瞧这情形,今晚许有风雪。”
穆槐听到声响,拿着灯笼,往坡上一照,还真发现一只信鸽到了,快奔过去,捉了鸽子递到夕榕的手里,夕榕取下一截用纸包裹的麦秸:“这是续骨膏!走吧,推我回营。”
二人回到营中,穆槐便去请了郎中,一起到了宇文旻的小帐,看郎中褪开宇文旻的断指,郎中皱了皱眉:“梦妃,伤口已经结疤,还要再续么?”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