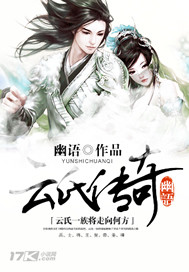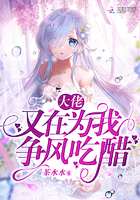中秋佳节,花好月圆。
本是阖家欢聚之日,可沈府上下却是一片惨白。夜间偶尔响起的风声,断断续续的啜泣声,轻轻飘荡的白幡,更显得这座宅子阴森可怖起来。
夜已深,沈昭由析玉搀扶着回到了自己院子。
她今日在灵堂跪了一日,身子一时间还缓不过来,膝盖处有些僵硬,行动时便略有不适。
好在明日一早,沈老太太的灵柩便要出殡,他们这些孙辈也不必日日在灵堂跪着了。
听小佛堂服侍的仆从说,老太太是自缢而亡。
从嘉福寺回来没两日,便突然在一天夜里悬挂白绫。等到第二日一早,进去服侍的嬷嬷看到时,都差点吓得两眼一白,晕死过去。
对这事,谁都没有防备。
因为被关进小佛堂的那些时日,老太太虽提不起多大兴致来,可精气神还是在的,至少不像是会做出自缢的事来。
谁曾料想——
沈昭靠坐在软榻上,不远处的黄花梨木几上灯火轻轻跳跃,照得她的神色忽明忽暗。
“天色已晚,姑娘快去歇息罢。”
析玉铺好褥子过来。
沈昭却没有那份心思,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你说那是巧合,还是什么?”
“嗯?”
析玉乍然听她说话,一时间倒没反应过来。
沈昭神色莫测,又接着说道:“那日老太太去了嘉福寺,紧接着程景濂也去嘉福寺进香。她回府没几日,又自缢而亡。”
析玉听得此言,不禁被吓一跳。
“姑娘怎会这般想?若是老太太真与首辅大人有瓜葛,又怎会……怎会落到这个境地?”
“是啊,她何必。”
沈昭摇摇头,脸上露出冷意来。
“死无对证,真是可惜。”
析玉却被她这略显笃定的话弄得心神不宁,她迟疑了一会儿,终是忍不住问:“若是老太太和首辅大人之间……那她又是为哪般呢?还有之前那位蒋侍郎,只怕……”
沈昭微冷着眼,面露不豫之色,“连身边的老嬷嬷都走了,真是一干二净。”
这是说沈王氏身边查不出什么来——在沈王氏自缢的第二日,她身侧服侍多年的王嬷嬷便跟着投井。说是怕老太太一人上路太孤单,陪了数十年,这黄泉路自要陪着走。
但其中是非,怕是唯当事人知晓。
沈昭只好顺着蒋尚穆那条线接着查,虽然心中隐有猜测,可到底摆在面前让人心安些。再者,假若程濂与沈王氏真有勾结,其目的又是——
她猛地想起早已被遗忘的季方平,以及崔逊曾同她说过的话。从一开始,程濂便在追寻国玺的下落,这般行事亦无可厚非。
可眼下沈老太太自尽,又是何人之意?又或者他们已寻到了国玺,所以才……
沈昭觉得这想法荒唐可笑。
若真已寻到,第一个乱定是沈家。
可如今的福建却是风平浪静。
她压下心底冒出的那一点念头,等着老太太出殡。
谁也不知道,在与沈家隔了数个坊市的明照坊程府庭院深处,有一人趁着夜深人静,月色暗沉,悄悄点了香烛和纸钱。
一时间夜寂无声,唯有青烟袅袅升起,星火跳跃,仿佛是故人轻叹,岁月如梭,往事不可追。
……
沈老太太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里出殡。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雨下下来,天气果真愈发清寒。尤其是宅子里人稀言少,就更显得清冷。
沈王氏乍然逝世,谁也不敢多言,怕触了主人家的霉头。
沈昭是个例外。
还是如往常一般,打拳习武,练字下棋一样不缺,来了兴致亦会拉着沈清远探讨朝中琐事。沈清远原先还略感不适,可见沈昭所言发人深省,久而久之便已坦然。
这一日,沈昭又起兴致。深觉在院子里待着过于乏味,便大着胆子寻到沈清远的书房。
虽说几房分开住,这一片宅子也只有他们兄妹俩,可毕竟不是年幼无知,私闯外院也算得出格之举,只是无人管得了她罢了。
在书房守着的小书童看到她过来,倒是惊诧了一番,又想自家姑娘连女扮男装去学府读书都做出来,闯个外院算得了什么事?
当即便规矩地行了一礼。
“姑娘今日来的可不凑巧,少爷现下不在书房里头。”
沈昭怔了一下。
“我特地趁着休沐过来寻人,怎地兄长还不在?可是有何事绊住了?”
“是秦府的二公子,他趁着旬假在玉溪办了个雅集,约了同窗好友前去,名曰仿古人流觞曲水,尽抒胸臆。本来少爷还想将您唤过去,后来又思及永嘉侯世子……便作罢了。”
听到最后,沈昭总算琢磨出味道了。她似笑非笑地看着小书童,片刻后又问,“秦府二公子可是秦侍郎府上的?”
“正是。”
沈昭闻言,倒是有几分感慨。
想想也是,她都快满十六了。沈清远自是已及冠,到了适婚年龄。若非父母皆在惠州,只怕早已相看。哪能落到功名已成,却孑然一身的地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