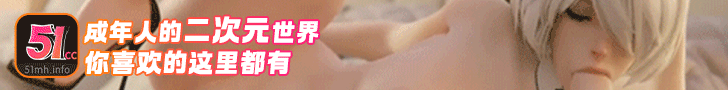冷风乍起,夜色正浓。
沈家正院的书房里却仍旧亮着灯,在这漆黑如墨的夜色里,更显得微弱,细小。
房间里传来不高不低地交谈声。
“你那日去长乐县怎叫人瞧见了?”
沈行恪坐在圈椅里,双手搭在扶木上。几缕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明黄色的灯火微微摇曳,更显得他的脸色忽明忽暗。
沈清俭和沈清豫皆站在书案前,垂手而立。
沈清豫微沉着脸,道:“他们约儿子在长乐县见面。您也清楚,长乐县本就是他们的地盘……倒没想到会让那后生撞见!您看现下该如何?”
沈行恪想起先前谈话之时,少年毫不畏惧的眼神,继而沉默了片刻,“他不敢说的。”
沈清豫有些意外。
“父亲怎会如此相信那后生?他可还知晓沈家的拳法,谁知道背后站着谁?还有此次来福州,他亦是行迹可疑。近些时日罗浮教又频繁同我们接触……谁也不知道会怎样!”
“沈家的拳法兴许不止我们清楚。”沈行恪沉声道,“至于我们同罗浮教有来往,与他一个余家子弟有何干系?他也是怕我们起杀心,才以此为依凭。”
沈清豫闻言蓦地一愣。
“父亲之意……他同沈氏族人有渊源?”
“沈氏本也不止我们这一支。”沈行恪微微颔首,又微沉着脸,“罗浮教的来历可打探清楚了?”
这句话是问沈清俭。
“他们近些年行事愈发没有章程,前些时日还劫持了季公覆之子。倒完全像是江湖人的作派……我们的人手一时间也觉察不出来。”
“你见哪个江湖人敢劫持朝廷三品大员之子?”沈行恪沉着脸,语气不善,实在是罗浮教行事过于频繁,如鲠在喉,令他颇感不适。
沈清俭顿时默然。
“我们近些年一直以沈家军后人自居,倒少有人寻上门来。可近来这罗浮教的态度却叫人意外。”沈清豫略带疑惑地说道,“罗浮教同儿子接触,竟多是询问沈家祖上一事,而无他事。”
他顿了一下,见沈行恪脸上神色淡淡,便又迟疑着说道:“儿子记得父亲曾说,是正始年间的动乱才致使家族分崩离析。而罗浮教传承已久,在承德年间便十分活跃……儿子觉得他们兴许是……”
余下的话他没有再说,可在场的人都能明白。
沈清俭沉思片刻后,亦微微颔首,“不无可能,否则他们何必同我们频繁接触?还记得前几年在辽东之时,初遇罗浮教,他们的态度便十分和善,对我们并无恶意。”
说到这,沈清俭沉吟少许,又微摇着头道:“倒也不能这般说,当时的罗浮教虽心怀善意,却是恭敬居多。可今日听三弟这般说,这态度与先前却是截然不同的。”
若只是简单的心怀敬意,何必打探沈氏过往?这些年,明里暗里探查沈氏的无一不是居心叵测之人。当年那段渊源,本不该流传至今。除沈家世代相传之外,只怕更多地是怀有异心,欲取而代之之辈。
因而,便是罗浮教再示好,他们亦不敢等闲视之。
沈行恪面上亦露出几分凝重来,沉默了半晌,才沉声道:
“此事确实不可大意。正始动乱之际,知晓内情的并非只有沈氏族人,多年过去,谁知他们是否起了异心?当年之人大多奔向海外,一直不曾见其踪影,怎会突然出现?还偏偏是诸皇子争位之际。”
余下两人便皆默然不语。
沈行恪的话确实有几分道理。
国朝眼下并未立储君,都言贤者居之。可若手握国之重器,就未必是贤者居之。谁都知晓大周慕容氏之所以被认为来历不正,除了谋权篡位外,主要是其手上并未有传承数代的国之重器。
传言,国之重器才是国朝气脉之所在,而慕容氏手中并无其传承,因而大周根基迟迟未稳。
此事牵扯甚大,他们并不敢轻易抉择。
“父亲,恕儿子直言。”沈清豫微沉着脸,神情间隐有困惑不满之意,“当年祖上为避开追杀,被迫迁居南下,多年来,我们这些后辈仍不敢正视祖上身份,唯以沈家军后人自居。
可据我所知,百余年前的沈家亦只是落了个凄凉的下场。既如此,我们何苦耗全族之力,守于此处?虽则沈氏历来为忠君之辈,可君不为君,肆意猜疑,我们又何须忠之?”
沈清豫此言颇有几分大逆不道之意。可却无半句不属实。史书上至今还记载着沈氏满门破败之状,可沈氏若真那般不堪,有何来今日沈家驻守福建之事?
沈行恪沉思了半晌,才缓缓说道:“多年来,我们沈家之所以守在此处,皆是因祖上所行之事,以待后来者,物归其主。然世事变迁,转眼已是百年。
可不论沈家祖上作何想法,沈家祖训又是何意,我们都不可随意从之,亦不可肆意违抗。前尘往事究竟如何,老夫并不清楚,活至今日,所见唯民生而已。
若是国泰,民无忧,沈家守之。若是国乱,江山倾,即便世上再无他人,亦要反之。你们必须知晓,沈家忠的不仅是君,更是国。”
两人闻言,亦是神情一震,齐声应好。
“那罗浮教该如何处理?”沈清俭忍不住微微皱眉,“他们行事这般醒目,总不能放任不管。如此频繁的来往,于他们无多少害处,于我们却是倾族之祸!
今上本就对我们沈家功勋过重,略有不满,自践祚后,更是频频打压。今日,余家那后生的言语若是传出去半分,怕是都会引起猜疑。”
沈行恪的脸色亦不太好看,“最近这些时日,朝中动荡颇多,就不必再同罗浮教来往。若是他们还有书信递来,便询问他们目的何在?
此事还需知根知底才行。他们若是不肯透露半分,我们也当作寻常往来,不必反应过激。只当不知晓内情,与他们虚以委蛇一番便罢。不过,罗浮教的底还是要探明。”
话落,他又摆摆手,示意两人退下。
片刻后,复又说道:“把尧哥儿唤过来罢。”
“夜已深,父亲为何还要……”沈清俭稍有些迟疑。
沈行恪想起先前的夜宴,便道:“余家那后生,老夫仍旧不太放心,还是询问一番为好。”
喜欢永明纪事请大家收藏:(www.xs4.cc)永明纪事全书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