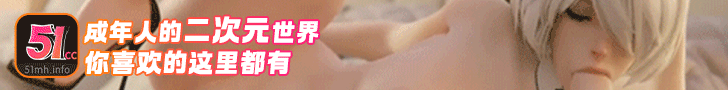这是沈昭第二次提及荀嘉。
第一次尚可认为是借荀嘉之举邀他一见,可此刻再提及,其中深意就值得琢磨。
他忍不住抬眼像沈昭看去。
却见对方只是端起清茶轻抿一口,神色十分淡然,更没有急于求一结果的迫切。仿佛这只是她闲聊之际想起之事,而他答或不答,皆无大碍。
慕容祁一时间反倒拿不准她之意。
再者,荀嘉作为他的幕僚,向来是隐于人后,声名不显,怎到了沈昭这儿,反倒值得注意?
他默了片刻,才缓缓说道:“我听闻姑娘今日相邀是为感念我命人守护余宅之事,故而前来一叙。至于与之不相干之人,何须相见?”
沈昭听闻,挑眉一笑。
“听殿下之言,似是对这位荀先生倒是颇为爱护。世人皆言,相识于微末,情深于海,可见诚不欺我也。我原是仰慕荀先生之风采,欲于今日与其一叙,如今看来却是我妄想罢了。”
慕容祁听闻,神色间隐隐露出不豫之色,“一介白衣,即便颇具才识,终有困顿之处,何足挂念于心?”
沈昭但笑不语。
她说了这么多,若慕容祁还以为她只为见荀嘉一面,也未免太让人失望。
慕容祁自是知晓其中颇有蹊跷。
沈昭与他本无交际,若非同余怀梓结识于微末,又有利益纠葛,以对方之脾性,未必肯屈尊见他一面。对方的身份虽不起眼,可她搅起的风浪仍是足以令人侧目。
只是对方今日,话里话外皆是荀嘉,并不涉及其他,倒像是借他之手有意探寻,这让他心生疑虑。
“姑娘数次问及荀先生,可是此人有不妥之处?”
沈昭的神色骤然一松,淡淡地笑道:“非是荀先生有不妥之处,我只是发觉荀先生之心性魄力非常人可比,这才略感惊奇。”
她顿了顿,又问,“我听闻荀先生原是南直隶人士,举子之身,后因眼见官场之险恶,才决定从此只读三千圣贤书,不问窗外纷扰事。却不知他最终如何会跟在殿下身侧?”
沈昭这般说,显然是已打探过荀嘉的底细。只怕知道不比他少,既如此,又何必再询问?
慕容祁便轻声笑道:“姑娘既知荀先生之过往,自然也当清楚,他之所以留在我身侧,只为一场知遇之恩。当年于京郊野外,我乃失意潦倒之徒,郁郁不得志。
偶见荀先生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坦然坐之,深感其气度不凡,故出言问之。始知我等同为天涯沦落人,不禁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交。这才有事后入府一说。”
他微微笑道:“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荀先生此举唯从本心罢了,并无特别之处。”
沈昭未曾料想慕容祁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倒是怔了一下,而后才轻声说道:“殿下此言在理。既是知己,行事当凭本心,自无需过多计较。只是殿下将其当作知己,他却未必同礼相待。”
闻得此言,慕容祁脸上顿时带上了冷沉之色,略显冷淡地看向沈昭,“姑娘缘何对我这名不经传的幕僚如此好奇?可是他何时行事不大妥当,使你心生不悦?”
沈昭见此,嘴角便泛起一丝冷笑。
“自有不妥当之处,我数日前得七表兄来话,似乎是他之前曾向殿下传信,可其暗卫却遭荀先生拦截,过府不入。我今日只欲询问一句,莫非殿下身侧的幕僚皆有如此本事么?连传给您的消息都可轻易阻扰。”
慕容祁闻言不禁愣了一下。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接话。
幕僚虽说是白衣卿客,可终究是仆,哪有仆从阻扰主子行事的?只是他与荀嘉相识多年,早已熟知彼此心性,他偶尔的出格之举,他自是不以为意。
却不想沈昭今日会特意提醒此事,倒使他心中隐约怀疑,自己过往的态度是否是过于纵容对方,以至他不知分寸,贸然行事。
“此事确实是荀先生思量不周。”
慕容祁面露谦意。
这声致歉倒不突兀,他同余怀梓并非主仆,贸然监视对方,实在是欠妥。
至于这歉意几分真假,沈昭暂且不管,单只看他眼中有思索之色,却无恼怒之意,便清楚对方根本没有将荀嘉的举措放在心上。
足见彼此间确实情深义重。
所谓疏不间亲,纵使慕容祁同荀嘉名为主仆,可还是比她这陌生人要亲近,她深知再说下去难得好结果,便只淡淡地提醒了一句。
“我深知殿下与荀先生相识于微末,情意之深非常人可比。但到底主仆有别,若荀先生轻易可替殿下做决定,往后殿下行事岂非多有不便?殿下对此应多思量。”
她见慕容祁并不言语,便又苦笑了一声,神色间颇有难堪之意。
“今日这番言语,虽说是不满荀先生擅自做主,于余宅盯梢。可说到底,终究是我行僭越之举,万望殿下勿要放在心上才是。”
“何出此言?”
慕容祁摇头一笑。
“我这些年于府邸静心养性,难有脾性相投之人。不瞒你说,端越实则是我为数不多的挚友之一。我与他虽因旧事而识,可情义却非比寻常。荀先生之举让他偶感不适,我确实该致歉。”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