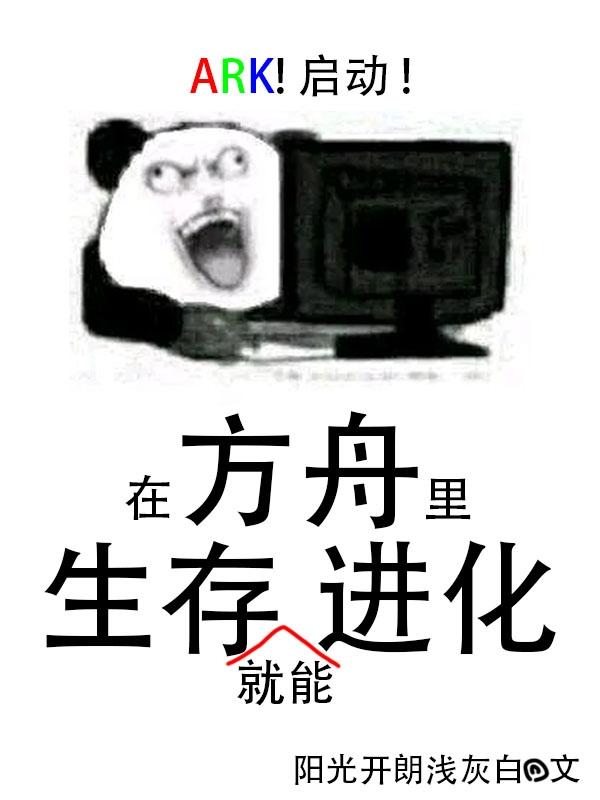局已布下,可能否达到期望的效果,还需要更细致的推动。
这几日,沈昭都待在府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她把析玉喊过来,询问外头的情况。
析玉便仔仔细细地回了。
“……现下金陵城内的文人都已是满腔愤慨,指责季大人为官不正,荒淫无道。听说豫东学府的学子也聚在一处,议论季大人这些年的恶行。有人提出要写万民书,上达天听,控诉其恶行。
前两日,翰林院姜大人在茗客居品茶之时,听闻此事后,亦言季大人行事不正,妄为天子臣下。又言程首铺为官清廉,不忘民生疾苦,季大人身为其外甥,如此恶行,实为败坏其名声。”
“翰林院姜大人?姜义权?”沈昭忍不住露出诧异之色来。
她对姜和的印象只停留在季府宴会之上匆匆一瞥。只知对方颇有血性,耿直有余,圆润不足,否则,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便不会出声。左右逢源之人可不敢同季家作对。
不过现下看来,对方未必是只知鲁莽不懂进退之辈。
像他今日这番话,只言季方平为官不正,中饱私囊,祸害此地百姓。却丝毫不提其背后所站程党,甚至于要说程濂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而季方平此举败坏其名声。
言下之意便是,此次民众愤起而击,非程党之故,只因季方平做法太过狠绝,让两淮地区的百姓都无活路可言。
此事完全是民愤而起,而非党争。一旦非党争,程党中人放在此处的目光便会少许多。甚至只会想着压下此事便好,至于其根源,追寻与否,都不必过多注意。
这才是沈昭想要的效果!
姜和这三言两语不知是误打误撞,还是刻意为之。或是他从这些言论中嗅到了他人操纵的味道,若真如此,便是沈昭也不得不佩服其敏锐。
她想时机已到,也该去豫东学府走一遭了。
……
沈昭刚到学府,周谨等人便围了上来。
“少明,你可算来了。”
神色间皆带着几分急躁与欣喜。
倒让沈昭一愣,稍带疑惑地问道:“你们……这是怎么了?莫非我不在的这些时日,学府还发生了大事?”
“学府无恙,不过大事倒有一件。”周谨便在一旁回道,又略带责怪地看了余怀忱一眼,“你同少明住一起,少明不出门,你怎不将此事告知她?”
余怀忱顿时垮了脸,在心里直喊冤枉。沈昭可是个姑娘家,他一大男人,哪好意思时不时地往她闺房里跑,又非亲兄长?
不过当下也只得略带歉意地道:“我见少明近来太累,便不好以此事打搅她。”
周谨便不再多言。
只道:“少明久居府邸,怕是不知如今整个金陵城都快闹翻了。前些时日,两淮盐运使季大人提升盐价,使得物价大涨,民众难以承担其价,生活愈加艰苦。
我等学子熟读明理书,修习圣贤道,岂能将如此荒诞之事置之不理?因而近来便想着状写其行,控诉此事,令其上达天听,听候陛下处置。
可前两日,我等上街同人说道此事,竟遭到了学府先生的呵斥,甚至有数名同窗被其处罚。倒叫我们几人深感不解。少明,你说此举有何不可?”
沈昭看着他们脸上的激愤之色,心想她此刻若说不可,怕是会被其围殴。兴许这才是少年人有的模样,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敢言敢行。这才是真正的不惧权势罢。
“并非不可。”她摇了摇头,“只是你们用错了法子。言事尚可,却不能过激。再者,我们现在身为学子,读书才是正道,便是言事也该充分利用习书之余,而非贸然行事。”
不过她虽这般说,却知学府未必是这般想的。
兴许是担心他们遭人利用,以致引起动乱,才呵斥一番。可此事岂是轻易能够压制的?学府亦是心知肚明。这般做不过是为了应付朝廷。届时便是真有人怪罪下来,说一句已尽力便可。
周谨等人听闻都有些赧然。
他们行事之时确实不曾想过这些,有些人甚至于连具体情况都不甚清楚,便跟着痛斥季方平。说到底只是想一展身手,或是展现自己不畏权势,敢于言事的风范罢了。
少年人大多是冲动的,会有此举并不意外。
不过,此事亦是沈昭所求之成效,当下便不再说教,只沉思了片刻,问道:“季兄现下如何?”
“他啊,此刻怕是羞愧欲死。早已不敢出门。”回话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此刻正面露嘲讽之意。沈昭对他有几分印象,原先同季桐走得近的一官吏子弟。
她闻言,便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她可不信这人原先不知季方平是何人,不知季桐是其子。原也是沆瀣一气的,如今倒自诩为清正之辈。
不过这亦是世事常态。
她复又问道:“重行既说要写万民书,那这执笔者可有人选?该如何定?”
周谨闻言便叹了口气。
“此事还未定下。我等不擅笔墨之事,怕无法真正写出其罪状,反倒使得对方逃于法度之外,届时便是得不偿失。再者,此事事关重大,若不选出德高望重之辈状其罪行,怕是难得成效。”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