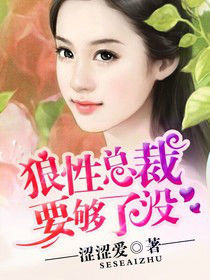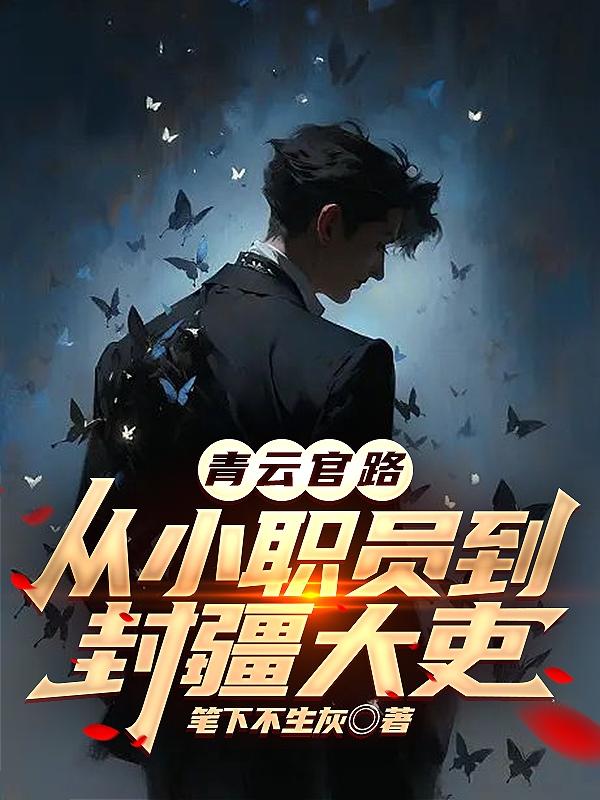永明十四年九月初,皇十四子禛因事囚于府邸,非诏不得出。
据朝臣弹劾,其主要罪行有三。
其一,私铸铜钱,以铅充铜,换数倍之银,扰乱银钱之平衡,动摇国之根本。其二,勾结内官,刺探宫闱秘事,散布不敬之言。其三,联合外臣,构陷至亲血脉,排除异己,以争储位。
其行径之恶劣,其后果之严重,罪不容诛。但天子念及父子血亲之情,感其诚心悔改之意,免于死罪,遂囚于府邸,以求自新。
这可不是以往的面壁思过那般简单。慕容禛不曾封王,削无可削,罚无可罚,但被囚禁于府邸的举措,等同于贬为庶人。
听说郑贵妃曾自解金饰,身披素衣,于殿外跪求崇仁皇帝。反被斥责,言其处贵妃之尊位,行粗鄙之事,不遵礼法,有失颜面,遂降为嫔。
为自己亲生儿子求情,又哪顾得上有没有颜面?郑氏所为于母子至亲而言合情合理,到崇仁皇帝那里却成了不遵礼法之辈,可见心中对慕容禛之厌恶。
只怕他此生已与储位无缘。
这般变故来得太快,不禁群臣未曾预料,便是曾经有意支持慕容禛的程濂亦是防备不及。
这原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慕容禛是该失宠,但绝不在此时,他在眼下这种情况下被贬为庶人,是逼着慕容祗和慕容祁上位。可这样一来,形势就更难掌控。
慕容禛一旦失势,慕容祗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朝最受宠的皇子,且有诚意侯等人在后,储位定可一争。可以崇仁皇帝之心性,若真有意让他们承袭,早已下旨封储,何以至今时?
因此慕容祁必然会重获恩宠。
可到那时,程濂手中却无筹码,隐现败落之象。因此,要说谁最不希望慕容禛失势,却是程濂无疑。
但事已至此,他此前防备不及,如今就只能追寻始作俑者。
私铸之事有迹可循,被人捉到把柄并不奇怪。但勾结内官,监视御书房和谋杀朝廷重臣之事,甚至于连朝臣名单都摆得清清楚楚,就没那么容易了。
除非是慕容禛身边出了细作。
且这个细作还知晓慕容禛所有事情。但就眼下的情况来看,并不能看出谁是细作。此事之后,慕容禛府上的长史幕僚或是获死罪入狱,或是削职为民,无一幸免。
更要紧的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也觉察不出来——因为两位皇子都可从中获利,谁都有动手的可能。至于有无这个本事……单看靖安侯旧案,便知慕容祁贼心未死,手中人脉定不在少数。
而慕容祗则更不必说,他有诚意侯等人扶持,早已与慕容禛不分伯仲,未必不是他所为。可惜程窦党皆未真正将心思放到他身上,一时间竟防备不及。
但这件事首尾断得太干净,让程濂深感异常,他不禁给岩溪先生去信。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因为窦党也未插手此事,他们两党都是始料未及,最终又袖手旁观,并不知晓实情。可照岩溪先生之意,还是只能等待,等大长公主逝世,等崇仁皇帝老去,等慕容祗势大,再伺机而动。
程濂别无他法,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虽则他手中没了筹码,可争储之事到底只是个幌子,只要仍处内阁之首,崇仁皇帝恩宠不减,文武百官俱从他之号令,又有何可忧?
但世事总是多变。
程濂的安稳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西北暴动,榆林城陷。
榆林总兵杜巩上书请罪,自言管辖不及,致使奴隶出逃,于街道犯事,多名官员受其戕害,命丧贱奴之手。甘愿受罚,唯望陛下斥责,以恕一身罪孽。
这份奏折跑断气了好几匹马,被八百里加急送至金銮殿。
然未等查明情况,榆林监军又传奏折于天听。而是榆林官员监守自盗,借职权之便置办奴隶场贩卖奴隶,以获巨资,其次又于城中暗设角斗场,命奴隶互相搏杀,胜者自终生免除奴籍。
受到戕害的榆林官员正是在角斗场观赛之时,被奴隶暴起而击。而监守自盗者则是以榆林马市提督官程度潇为首的一众官员,其中还包括榆林总兵杜巩在内。
听说崇仁皇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几乎昏厥,显然已是怒极。
他如何想得到,自己亲命镇守边疆的将士,竟这般淫佚无度,行如此惨无人道之事,简直是无视天子谕令,将国朝法度弃于陬隅。
让他们镇守边疆,护住大周的江山,他们却寻这样的法子来作乐。全然不顾及国朝的规章制度,更未将他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何其荒谬!已是罪不容诛!
他随即下令彻查。
而当程濂拖着一身老骨头来御书房外求见时,崇仁皇帝却是不留半分情面打发回去。
直言子不教父之过,程度潇行如此荒唐之事,与他这个父亲脱不了干系。事已至此,合该回府,闭门思过,已赎己身之罪孽,以何面目陈于君主?
可见崇仁皇帝心中怒极,连这个辅佐他多年的老臣脸面也不愿顾及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