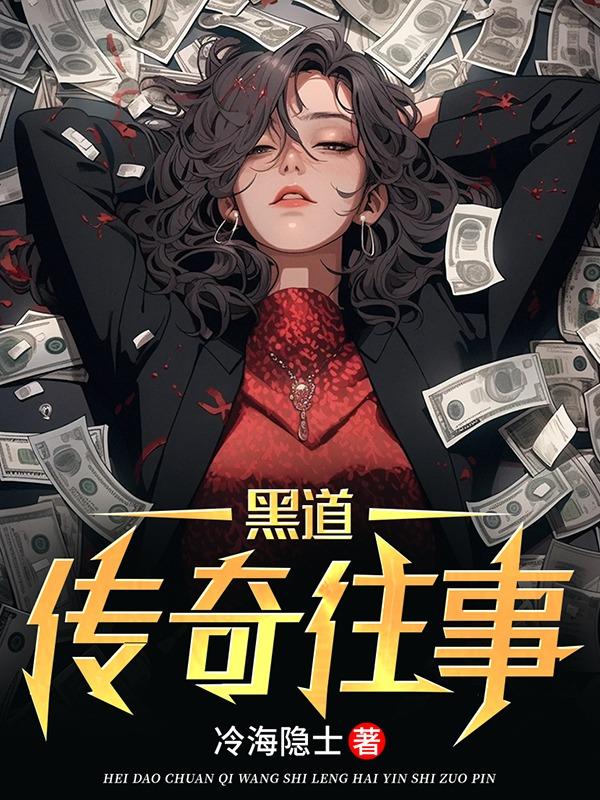永明十三年的九月,沈昭伴着纷飞的落叶回到了京师。
自永明十二年开春离京,至今已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京师的局势便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发生变化。
比如吏部右侍郎病逝,窦敬言上书请广东布政使廖思浦回京,调任吏部右侍郎,崇仁皇帝应允。湖广布政使谢时镇入京任礼部侍郎,由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升右都御史衔接任。
如詹事府少詹事韩绩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季槐升任通政司参议,孟湛升任詹事府左春坊庶子。户部主事罗松生升任户部员外郎。
前些时日福建省水患频发,百姓生活艰苦,布政使尸位素餐,不谋其政,中饱私囊,崇仁皇帝知晓后立即将其罢免,随即令左参政升任布政使,掌管福建之民生。
因福建道官员良莠不齐,私谋其事,不理朝政,遂命福建道监察御史陆世蒙外任福建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督察百官。
沈昭收到消息时,回京没有两日。
她立即让人着手去查了福建的情况。
原福建省布政使是早已致仕的工部尚书的门生,自他不在朝中为官后,行事便有所顾忌。偏生福建这块地方谈不上富庶,素日里水患倭寇之乱又多,上头还有巡抚总兵压着,并无多少实权。
他那份投名状即便是递,也不知递给谁。程窦两党不接,对韩廷贤等人又无甚好感,便一直拖着,拖到这次出了事,才想起来要拜祖宗,却无人理会。
崇仁皇帝也恼了福建三番两次的出倭寇之乱,还让人传了旨意给福建巡抚总兵以及都指挥使,将他们都训斥了一番。这些人多少管着福建的军务,击退倭寇也是他们的主要职责。
虽说此次是出了水患的事,可倭寇趁机作乱却是不争的事实,自然是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便联名上了请罪的折子,崇仁皇帝嘴里骂的狠,却不敢真的撤了他们的职。
不说别的,单说都指挥使沈行恪便是早已威名震震的抗倭名将,再者福建总兵周辽亦是行军布阵的高手,没了他们,这福建不出月余就该让倭寇给端了。
这一番训斥请罪都不过走个过场。
而布政使刘登命虽保了,却是官降数阶,直接安置到云南的直隶州任知州了。可那地方不仅条件艰苦,动荡也不少,福建是倭寇,那里便是山匪。
若做不出政绩,只怕这辈子就熬在那偏远之地。刘登当即便丢了半条命,号啕大哭起来,可事已至此,绝无回旋的余地。
却叫众人更是认清了一件事——还是朝中有人才好办事。否则,就凭这小小的水患,何以至此。即便附近村庄因此被倭寇袭击,可福建那地方几时少了倭寇袭击之事?
连人都没死几个,不过今年上缴的粮食少了些,哪里就算得了大事?
想前两年广东省的时候,连着几个镇子都毁了,廖思浦不还做得好好的,就算御史的折子再怎么落,也不曾伤其半分。如今还入京做了吏部右侍郎,可谓是时来运转。
也有人说,刘登确实倒霉了些。谁让他挡了人家的道呢。此次升任的布政使的左参政正是左都御使赵鉴的胞弟。人家赵御史的胞弟想坐这个位子,这原来坐的人自然是挡了他的路的。
又有人说,这左参政升任布政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想那刘登任布政使时一事无成,先不说有没有剿倭,至少连这一方百姓还没护好。而左参政呢,在倭寇袭击村庄时,还设计杀了几队倭寇。
崇仁皇帝知晓后,还夸其勇猛有为,没有辱没大周朝臣的名头。言下之意便是指刘登懦弱无能,听说他在外头游玩之时,曾遇到过倭寇的队伍,却被其吓得两股战战,不能抬脚。
简直丢尽了大周的颜面。
沈昭知晓后,一笑置之。转眼又去查了其余几人的身份。
周家,沈家世代驻守福建,自不必多说。而掌管刑台的按察使是已故吏部右侍郎的门生,并未依附党派。至于福建巡抚潘仪德则是程濂的连襟,与程党关系自是亲密。
也难怪刘登在这场争端中毫无胜算,毕竟巡抚力压三司,位高权重,这福建早是程党的囊中之物。如若不然,程濂当时亦不敢让季方平在福建行私运之事多年。
地方官和京官到底哪个好,实在是说不清的事。
像京官,素日里有不少人打点,尤其是六部官员,手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敛财方式,京师又是富庶之地,且又在天子跟前,若是得其青眼,兴许哪日便会升迁,这待遇着实不差。
可地方官亦有地方官的好处。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像京畿之外的地区,即便这崇仁皇帝的手再长,只怕也管不了那么多。还不是任那些一省之长官胡作非为,欺压百姓?
就像程党之中,有程濂,赵鉴这样的京畿重臣,亦有潘仪德和赵钦这样地方大臣。可福建这块地方,握在手里好虽好,却不必花这样的血本。私运之事固然赚钱,可倭寇之乱也不是那般好除的。
却不知程党牢牢抓住,又能从中如何获利?
沈昭沉思片刻,最终只得静观其变。
陆世蒙此人是有名的诤臣,既然崇仁皇帝派他巡按福建,他自然也督察出名头来,那些人若想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行那龌蹉之事,只怕不易。
她随即将此事置于一旁。
眼下更要紧的还是面前这份名帖。
孟妧的婚事定在了十一月初,还有不足月余的时间,因此在她即将出阁之际,想要邀请相识的姑娘们去孟家府邸一聚,毕竟往后去了皇子府,想要再来往就难了。
沈昭看到这份请帖时,头都大了。
她跟孟妧的交际实在是淡得很,不仅淡且还是结了死仇的。她这般邀请,岂是心怀善意,只欲叙旧那般简单?可贴子已下,她若装病不去——面上却不太好看。
她在京师出阁,因此孟大太太和孟五奶奶等人都到了京师。原先在惠州府时,沈行书受了孟家的恩惠,又同孟家五房交好,孟家对她也着实不算差。
若不去,岂止是不顾及对方颜面,更是失礼。再者,自孟家长辈进京后,她怕惹了不必要的麻烦,只送了礼节,人却不曾上门拜访。
眼下,孟妧既然亲自请了她,焉有不去之理?
喜欢永明纪事请大家收藏:(www.xs4.cc)永明纪事全书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