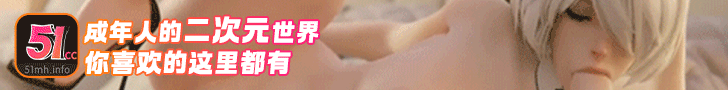她坐在轮椅上,脸上还有被擦伤的印痕,她的腿上盖着一条洁白的羊『毛』褥子,让人瞧不见她究竟伤有多重。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宇文旻快走几步,在她的身前蹲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夕榕却不再看他,仿佛面前这一抹夺目的红根本就未入眼底,跃过他的身子,她望着远方:“你、我之间,恩怨交织,我倦了。太子为我,牺牲了那么多。这一次,你如此狠毒,亦到了你我做个了结的时候。校场见面,不过是一种方式,了结你我之间的一切才是结局。”
她是夕榕!
他见过她的平静,见过她在白龙县如何冲入霍烈的包围圈。
她悠悠轻言,似用尽所有的情感,又似仅仅是感慨:“有人曾说,如果发现情感已成为一种负累,不再是昔日的滋味,可以释然地选择放手。因为相离不一定是背叛,给彼此一个美好的祝福或许都会海阔天空。”
她的淡定,却是他的心『潮』高涨。
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女子,看着她脸上、脖颈处的累累伤痕,还有她身上散发出的浓浓『药』味。
这一次,他真的伤她如此之深!
“你是夕榕,你真的是……”
打断他的话,她冷声道:“如若璃王殿下已等不及了结,那么现下夕榕便告诉你:我不再欠你了。”她回过头去,对身后的哈庆道:“哈庆,推到我前面走走吧,我想到校场看看。”
宇文旻看着她从自己的身前走过,她不愿再看他一眼,哪怕只是一眼。
月苑里的女人说:“不想世间有个和她一样的女子”只因,那是“夕榕”少有对他提出的要求,他便令楼三去杀她。
命运,竟和他开了一个这样大的玩笑,是这样大的玩笑。
宇文旻看着不远处站着的乔凯旋,抓狂地问:“告诉本王,梦妃怎么了?她怎么不能走了?”
乔凯旋瞧见宇文旻与夕榕说话了。“殿下脸『色』很差,还是早回帐中歇息。”
乔凯旋是太子府的人,他不愿说,谁也追问不出来。
宇文旻浑身乏力地回到自己的帐中,着令穆槐去打听。
穆槐回来后,便将这两日在军中传扬的故事细细地说了一遍。
怎会是这样?
他居然连深爱的女子都分辩不出真假,假的当成真,真的却险些丧命在他的手里。
夕榕,夕榕!
他念着这个名字,心痛欲绝,与“夕榕”那一夜的美好,全都变成了闹剧,成了他对她最致命的伤害。
那个女人,居然是假的!
她是假的!
宇文旻只觉连呼吸都可以刺痛心扉,冷得要将他变成一个冰人。
忆起回来地,瞧见她坐在椅子上,宇文旻问:“她的腿……怎么了?”
穆槐沉默一会儿,道:“奴才特意打听过,没打听出来。只听人说,她的腿伤得很重,太子殿下为此很是生气,昨儿早上不知为何还怒斥了五殿下,直到今天五殿下都没出过帐篷。”
一切都变了模样!
他伤了自己此生最爱的女人,带给她的伤害一定很深,否则她不会说出“了结”的话来。
这一夜,宇文旻辗转难眠,忆起对她的伤,便无法阖眼。
在小帐里,夕榕手里捧着本闲书,翻看了几页,便又放下了,她也是一满腹心事。不是为宇文旻,是为了宇文昊。
他竟然骗了她!
瞒得这样的好。
若非几位皇子姬妾在酉时来探她、闲聊,她不会知晓,他在骗她。
女人们最爱谈的话题,无非是如何打扮、衣服、丈夫、孩子,千古皆然。
他们在一起时,没说几句便又扯到了府里的姬妾身上。
五皇子的姬妾,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突地说道:“要说幸福,当然是梦妃了!直到现在太子府最尊贵的女人还是梦妃呢?虽不是太子妃,太子殿下可没允别的女人越了梦妃去。”
八皇子的杜妃则忙忙笑道:“可不就是,就我们府里,现下都有十一个姬妾了。我倒乐意跟着八殿下出来,省心多了。”
在众姬妾将要散去的时候,夕榕特意寻了个藉由:“李昭训,陪我坐会儿吧!”
夕榕遣了哈庆去厨房取吃食,小声问道:“你、我都是女人,你与我说句话实话,你之前那话是不是说……太子殿下……府里还有别的女人?”
李昭训忙忙摇头:“不管我的事,我可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不敢呆得太久,生怕再惹出什么事业,李昭训似逃跑般地离去。
他说,她离开后,他克死了两个女人,可他府里显然还另有其人。
是谁?
想到这个问题,直扰得她心神不宁。
哈庆见她闷闷不乐,抱着把古琴进来,笑嘻嘻地说:“这是从杜妃拿来的。”
夕榕很少弹琴,若非那日储少良引得她跃跃欲试,她也不会再碰。“好好儿的,拿琴做什么?”
哈庆把琴放下:“就当是拿来给梦妃解闷的。”
她看了眼琴弦,指头一拨,琴声清脆悦耳:“杜妃的琴,当真不错,连这音质也这般好。”她吐了口气,道:“你推我到帐外走走罢!将士们也很辛苦,我就弹一曲轻松的《牧羊曲》。”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