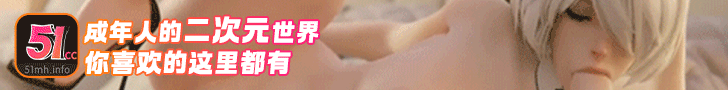屋子里,宇文昊蹲下身子,正要解开夕榕腿上的布,夕榕道:“让郎中来吧。”
“昨晚在林子包扎的,本该一早请郎中,却听说昨晚城外有急诊,郎中要今晨才回来。”宇文昊似在解释。
郎中身子发颤,有些不听使唤,道:“公子说得没错,昨儿老朽黄昏就出城了。”
郎中褪开腿上的布,便见小腿二上有一道极深的伤口,白肉外『露』,还在不停地冒血,仿佛是张着大嘴的猛蛇,甚是怖人。
小厨娘惊呼出口,用手挡住自己的眼睛。
夕榕低头看了一眼,微微眯了眯眼睛,“就劳张郎中,帮忙缝上两针,瞧这样子,如果不缝针,许是难以痊愈了。”
“昨儿老朽出城,接诊的是一个难产的『妇』人,前些日子配的麻『药』已经用完了。”
“不碍事,我能受得住。”夕榕微微一笑,“那他们可母子平安?”
“已经熬了两日了,老朽按照陈捕头说的法子用了。”
“剖腹产?”夕榕惊呼一声。
郎中取了干净的白布,又拿了『药』粉,弯曲的针,上面还余有特制的线。“老朽一说那法子,他家里人都不同意,非说那法子是用在畜生身上的,可那产『妇』自己倒也乐意。附近的稳婆、产婆请了三个,个个都没辙,老朽也只好试试了,从那产『妇』肚子里还真取出一个大胖小子……”
夕榕与这郎中相熟,他用银夹取了布块,沾了烈酒,一点点擦去血渍,又倒了大半瓶止血『药』粉在伤口上,烈酒浸入伤口,撕裂般的疼痛着。
宇文昊伸出手来,任她握住,她死死地抓住宇文昊的手,不再低头俯看,郎中继续与她聊着天:“取出男婴时,方晓胎儿的脐带缠绕在脖颈上,再晚一刻,怕是母子都得丧命。只是陈捕头,这种剖腹取胎,母子虽然保命了,那『妇』人往后还能生么?”
“五年之内不能再孕,需待伤口复原。五年后再孕,且只能剖腹产子,否则不然,宫床暴裂,就当真是一尸两命了。她这一生,只能生育两胎,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夕榕说着,只觉一阵钻心的刺痛,郎中穿针结线。
她的面容一阵紧过一阵的痛,双眉或疏或锁,握着他的手力道也越来越大,就连额上也渗现密密的汗珠。
宇文昊静默地瞧在心里,疼在心上,他曾许诺,护她一人,却终是能好好呵护于她。看她被人追杀,看她再次受伤。
小厨娘自是不敢看的,取了自己的帕子走过来,正要伸手给夕榕拭汗,宇文昊已先一步掏出自己的汗巾,小心翼翼地替她拭去汗珠,眸子里蓄满了柔情。
张郎中共缝了六针,夕榕低头时,看着上面缝合的伤口,越发像张嘴了,还是带了“牙齿”的嘴,这么长的伤口,待得好了,也会留下难看的疤痕。
张郎中道:“陈捕头的伤口极深,怕是得养三月方能康复。这十日,最好不要再走动,卧床静养为佳。”他停了一下,又道:“那天,陈捕头执意将成银柱一家赶走,城里的人都在议论纷纷,可现下老朽瞧来,陈捕头是想救他们吧?”
伤口缝好,张郎中依旧与她闲聊着,你一言,我一句,张郎中约有四十多岁,举止得体,一看就是个读诗书的人。他动作纯熟地替夕榕包裹上伤口。
夕榕越发觉得好受一些,也缓缓松开了宇文昊的手:“还是先生是个明眼人,夕榕做什么,你都清楚。说起来,还得感谢前些日子你给我配的『药』,若不是那些东西,也许昨晚夕榕就没命了。”
张郎中包裹好伤口,合上自己的小箱,就连这小箱也是夕榕建议的,他按照夕榕所绘,便自己做了一个,每逢外出诊病,就带上小箱子,倒也方便了不少。里面不仅有银针、创伤『药』粉等物,就连纸笔墨砚也一并备有,墨还装在一个小竹筒里,『毛』笔又多了个盖子。
“陈捕头心地纯良,老天自会护佑好人。”张郎中取了纸笔,走到桌前,写了张方子,道:“先抓两副『药』,吃上三天。三天后,再换伤口上的『药』。”
“辛苦了。”夕榕浅笑着,“梅子,跟着张郎中去『药』铺抓『药』罢。”
小厨娘应了一声,出了房门,刚出来便见一干人站在外面张望,胡师爷迎了过来:“陈捕头怎样了?”
“伤口已经包好了。让我去抓『药』!”
胡师爷笑说:“那你快去。”他轻咳一声,问:“陈捕头,晨食备好了,需要送到屋里来么?”
夕榕还不觉饿,忆起昨夜的惊险,还心有余悸,问宇文昊:“你许是饿了吧?”
宇文昊摇了摇头,抓起夕榕的手,深情款款地道:“这些日子,你受苦了。”
她低了低头,推开他的手,与张郎中聊了几句,也平静了许子。“军中不能没主帅,你还是趁早回去罢。”
宇文昊有太多的话想与她说,她已经忆起了他,否则不会哭得那么伤心。“要走,我们一起!”剩下的一句是:若留,我们也一起留。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